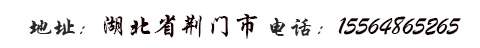纳凉作者耿勇
|
北京什么医院皮肤科好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140802/4439528.html纳凉 夏日,阳光总是热情火辣的有些灼人。 白天,树荫下象避风港,凉风习习让汗水放缓淫浸,冲淡了肆无忌惮的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 夕阳,吐尽最后热量,天空拉上黑沉沉的幕帘,月亮露出秀美的面庞,人们才纷纷出户兜圈、跳舞、嘻闹,尽情渲泄着,奔放着,让筋骨舒展,让汗水尽情冲开闸门,欢唱着带走多余的盐分。 舒坦之后回家冲个澡,看电视,上上网,享受空调带来的那份清凉。 躺在竹椅上,手拿芭蕉扇,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着旋律虽不够舒缓优美,却令人精神亢奋的歌曲,悠闲的等着时有时无的“穿堂风”的纳凉,似乎已成为记忆中遥远的残片,封存在怀旧的情感里。 幼年纳凉的记忆是残缺的,也是温謦的。在妹妹蹒跚学步,我朦胧似懂非懂的那些酷暑夜晚,没有电扇,消暑纳凉的唯一的凉风便来自母亲手上那把芭蕉扇,它是我们扺挡闷热唯一的依靠。 入夜,芭蕉扇下的凉风轻徐催我们入梦。母亲人累手酸,稍停片刻,我们便翻“烧饼”似的难以入眠。不知多少回,我总在熟睡中被母亲突然碰醒,醒来发现母亲总是侧卧着,用手中的芭蕉扇不停地为我们扇着,实在困了,打盹儿,一清醒,赶紧又扇起来,生怕热了我们。我们睡姿不好,相互挤压时,母亲温柔的手总是轻轻地抬放着我们小腿或小胳膊,然后轻抚着,摩挲着我们细嫩的肌肤,在月光下,脸上呈现出幸福和满足来。 那些日子,人们不惧炎热,精神亢奋,不惜流汗与它抗争,但日子过得难以从容,在大自然的烈日炎炎面前,总是急促和茫然。在我读初中时,总算家家陆续有了电扇,但家乡属内陆城市,盛夏之夜除偶尔有点雷阵雨,通常无风,常能给人带来凉爽幻觉的树梢,总是“定力”十足,纹丝不动。闷热得如同身置“蒸笼”中,电扇送出的风总是温热的,让人烦躁难以喘气消汗。 捱过烈日炙热,太阳西下,家家户户便在门前或不远处,找个地方,用井水或自来水,先泼上几遍,让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地面上的“热量”蒸发一下,然后放上竹制凉床。没条件的或家中凉床不够的,大都卷个灯草席,带个枕头,毛巾被,铺在人行道、楼顶平台上甚至机关大院大门边上,反正哪里有一丝凉风,哪里适意便睡在哪里。 梧桐树下,马路边的人行道最受欢迎。凉床、草席相连如同曹操率八十万水军,船头连着船尾,浩浩荡荡一样。蒲扇、说笑、咳嗽、拍蚊声、劣质烟草味……青年男男女女或坐或卧,说笑着聊着天,说到兴奋之时,你用芭蕉“扇”我一下,我用胳膊角“顶”你一下,打个情,卖个俏,谁也不介意,谁也不上心。天不分方圆,地不分南北,床席不分你家我家,小伙伴们常在哪聊,便在哪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拍屁股走人,谁家的床席谁收拾,谁也不会有怨言。因为按家乡话“都是家门口的”。 那时,各家的家境都差不多,富不冒尖,穷能见底,无富可仇,无贫可嫌,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如别人家放好小椅桌,纳着凉开晚饭,正巧你尚未用餐,主人会热情加双上碗筷,盛碗绿豆稀饭,客人也不客气,更不会拘谨,如同家人般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纳凉总少不了降温的瓜果,不过只要张家拿出从井中侵放的冰西瓜,红瓤黑籽,李家便会端来绿豆汤,珠圆玉润……当然小伙伴手上最多还是自制的炒西瓜子,吃着、磕着、聊着、笑着,没人在意炎热,或许内心里感谢上苍的恩赐,因为酷热,让人们不再像冬季那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而是开放自我,尽情享受着情感的交融。有多少情侣,在纳凉中埋下了情种,经过秋风萧萧的鞭笞,经过寒风凛冽的考验,来年春天开花结果。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js/10570.html
- 上一篇文章: 直发VS卷发风情美和知性美之间的比拼,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