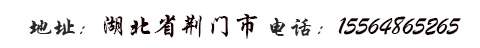山东名家郭保林腾格里的另一种解读
|
白癜风的偏方 http://pf.39.net/bdfyy/bdfjc/150917/4698007.html 郭保林,山东聊城市冠县人,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散文集《青春的橄榄树》《阅读大西北》《昨天的地平线》《千古墨客》《郭保林经典散文》等25种;长篇纪实文学、传记文学《高原雪魂—孔繁森》《塔克拉玛干:红黄黑》《谔谔国士傅斯年》及小说集等7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首届冰心散文(集)奖、第二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首届齐鲁文学奖等奖项。多篇散文选入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其创作成就载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国散文通史》等史学专著。 腾格里的另一种解读 文 郭保林 1 腾格里沙漠不属于宁夏,它的大部分面积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和甘肃的武威地区。横空出世的贺兰山以其雄浑的躯体遏止住了它东扩的欲望和野性的狂妄,留给银川平原一片绿色的安谧。但是在贺兰山和中卫山还未来得及衔接的一瞬间(这一“瞬间”凝固了,它们永远不可能衔接了),腾格里乘隙奔突东来,将一片沙滩愤怒地倾泻在黄河岸边,积高百米,向宁夏展露出它暴躁的情绪和狰狞的头角——这就是被世人称作的“沙坡头”。 沙坡头如今已成举世闻名的风景胜地。那一轮轮桀骜不驯的沙丘被聪慧的宁夏人用一米见方的“方草格”织成的巨大网络死死地罩住了。草格间栽满了耐旱的芨芨草、索索柴、骆驼刺和沙柳。远远看去像一片绿洲。一天,联合国的官员来到这里,惊叹道:“这是人类征服沙漠的典范!”于是沙坡头便名扬四海了。 我对沙漠并不陌生,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毛乌素沙漠,都曾留下我趔趄的履痕,来去匆匆,岁月匆匆,也许风沙早把它们抹平了,或者说沙漠早把我忘记了,但我还记着它们。萧萧漠风曾打疼了我的脸颊,炎炎烈日曾晒爆了我的肌肤。雄浑、寥廓、旷博,沙漠里蒸腾而出的那种萧杀般的苍凉悲壮气氛至今还弥漫在我的心头。 苍凉是天地河汉间之大美。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氤氲着苍凉的氛围,必然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因为悲剧最能展示生命最深刻的矛盾。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喜欢“光明的尾巴”,但西洋文学作品都重视悲剧的展示,“悲剧是生命充实的艺术”(宗白华语)。人生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万物毁灭的悲剧,总让人感悟出生命的痛苦,体验出更深奥的哲理。钟鼓馔玉、鸣钟列鼎的富贵,金堂玉户、琼楼仙阁的奢华,威加四海、势炎熏天的狂妄,到头来都是过眼烟云,留给后人的只是一抹苍凉。谁也无能力与时间抗衡。毁灭之神啊,你在吞噬一切! 好啦,现在我已走进腾格里大漠,穿过沙坡头绿洲再往前走,便看到腾格里铺张扬厉恣肆汪洋的面目:满眼是浩浩荡荡的沙丘,雷同化的毫无个性的沙丘犹如大海的波浪,汹涌澎湃地拍天而去。沙涛无声,煌煌大漠是一片起伏跌宕的空旷和静寂。西斜的阳光照耀着沙海,细沙反射着阳光,刺人眼睛。天空蓝得透明,几缕若有若无的白云,像缥缈的梦幻。大漠似乎被太阳煮熟了,蒸腾着热辣辣的蜃气,一种火的颤栗,一种凌轹的笼罩。贾谊客居长沙时曾感慨道:“天地为炉,造化为功;阴阳为炭,万物为铜。”我不知道此公在江南风景佳胜之地怎么发出如此感悟,如果是站在腾格里的沙丘上,此言更真切了。 时值四月,还不到燠热的盛夏。“四月是死亡的季节”。艾略特大概也弄错了位置,是不是把荒漠当成了“荒原”?四月的沙漠是沙尘暴最活跃的季节。我经历过沙暴天气,那是几年前在塔克拉玛干大漠。人在沙尘暴里行走,轻薄得像一张纸,像一个影子,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到空中,然后被狠狠地摔到沙丘上,生命转瞬间消失。地球上有十处沙尘暴发源地,中国占有两处:一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处是阿拉善的荒漠地带,也即腾格里沙漠。沙尘暴和地震、洪水、火山暴发一样,自古以来都末停止过,它是大自然万物消长的一环,是天体运作的一道程序。早在汉唐时代,沙尘暴就不断出现,边塞诗人岑参曾描述道:“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岑参描写塔克拉玛干大漠沙尘暴的情形,轮台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还有陈子昂“黄沙幕南北,白日陷西隅”,写的是河西走廊黄沙飞扬,疾风肆虐的场景。 历史上许多名城都被风沙掩埋了,罗布泊湖畔的米兰、尼雅、楼兰,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都化为了废墟,大夏王朝的赫连勃勃的皇都——统万城,建城不到五百年,就被沙尘暴吞噬了,还有繁华一时的黑城子,也早已成了沙尘暴囊中之物了。 现在风沙俱净。太阳已经西斜,沙丘沐浴在温和的阳光下,温情脉脉,那风蚀的沙纹犹如池塘里娓娓荡漾的涟漪。阳光照耀的一面,又像少女的胴体,闪烁着毛茸茸的红光,一种热烈的青春的象征。这时,我想起青海已故诗人昌耀的诗句:“黄沙丘,亮似黄昏”。 沙坡头紧逼着黄河,如果不是人工植草种树固定了一座座沙丘,怕是黄河也要改道了,这高达百米的沙山对滔滔北去的黄河是藐视的。据说沙尘暴频频发生,每一场沙尘暴都有给生命带来巨大的灾难。是沙坡头这片小小绿洲保护了包兰铁路,使其几十年如一日地穿越腾格里沙漠未遭厄运。但是人类在大沙漠面前毕竟是渺小而懦弱的,沙漠每年仍然以十几米的速度向黄河逼近。 “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眼前没有大漠孤烟,却有黄河落日圆的景观。 漠风轻拂,落日像燃烧殆尽的火球,火苗发出霹霹啪啪的声响,火星四溅,半个天空都灼红了。那一轮橘红的落日在掬水可以铸金的黄河波涛里沉沉浮浮,把一川风涛也烧沸了,浪花里迸溅着火星。天地苍茫,万籁俱寂,只有这苍凉的落日和古老的黄河弹奏一曲悲壮的乐章。 2 腾格里,蒙语的意思是天一样大。走进腾格里大漠,我只感到语言的苍白、贫乏。语言是难以沟通人与自然情感的。这大漠的空旷和寂寥、凝重和静默,你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沙漠不是死亡之海,早晨,你会听到太阳抖落一身沙尘,艰难升起的步履声;月夜,你可以听月亮钻出沙海的沙沙声。沙洼间,沙丘与沙丘间的平地上,仍有耐旱的芨芨草、骆驼刺、索索柴之类的生命,坚韧而顽强地生长着,该开花时开花,该结籽时结籽,它们仍然用生命注释着春夏秋冬的更迭,记录着岁月匆匆的脚步。 有一天,我在沙漠里看到一棵马莲草,我被它惊心动魄的生命惊呆了:它孤独地耸立在一个小小的沙墩上。绿剑般的叶子倔强地擞着,愤怒地直指苍穹,展示着生命的高傲和放达。它下部的沙丘被风蚀去,暴露出庞大的根系,绛紫色,像憋青的脸,竭尽全力地支撑着苦难,支撑着一棵不屈的生命。那扭曲变形的根须,纵横交错,绵亘迂回,使我想起了东山魁夷那幅名画《根》,想起了罗丹的雕塑《三个影子》,想起了但丁,想起孤苦零丁的苏武,想起了受苦受难的耶稣。 走近它,我肃然起敬,我觉得它不是一棵草,是一尊神,是一尊生命的力神和战神。晨风吹来,那坚硬的叶子发出金属般的铮铮的响声,像奏响一部巴赫的《马太受难曲》。 我站在马莲草身边,心里涌动着酸涩和悲苦,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身向它鞠躬:马莲草啊,“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这些年来我在西部跋涉奔波,我情感的河流里,总翻卷着凄苦的漩涡:这里的山,这里的树和草,这里的人和牲畜,从他(它)们的身上我感到生命的苦难和世界的末日的苍凉,也使我更多地感悟到生命的崇高,爱的崇高。 我想起塔克拉玛干沙漠那片原始的胡杨林,那粗大高峻的树木大多数都已干枯死亡,枝桠断裂,露出白生生的骨碴,脚下是乱七八糟的残臂断肢;有的只剩下半截树桩,——如果你俯下身仔细察看树桩的横断面,会惊异地发现:那浅色的年轮构成畸形的图案,忠实地记录着它的争斗、痛苦、疾病、炼狱般的苦难,艰辛的挣扎,还有幸福和繁荣……树是很聪明的,知道没有人记载它的历史,便悄悄地用年轮将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都写进它的自传。而今这些树木有的已枯死了数百年,上千年了,它们依然一动不动地挺立在沙漠里,像倾圮的神庙,像一场厮杀搏击后的古战场,这风景太悲壮太苍凉了。看到它,你会感到语言有时是人类最愚蠢的表达方式,人与大自然的对话,不能靠语言,最不可信任的是这些无生命的符号。 传说,塔克拉玛干的胡杨树,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只要有一条根,就拼命地扎进大漠深处,吮吸苦涩的水分,支撑着不死的树桠,绽出一片片嫩黄的绿叶。圆圆的薄薄的叶子像粘在树枝上似的,但是那是生命的信念,绿色的宣言。看到它们使人想到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出生、爱情、冒险、死亡的悲剧。 那天,我和一棵胡杨树做了一场感情的交流: 我:你为什么生长在这死亡之海? 树:这是命运。命运注定我生存这里。我父母年轻时,这里有河流,后来河流经不起风沙的袭击,逃亡了,只留下我们这些树。前面那棵是我父亲,后面那棵是我母亲,周围那些都是我的亲戚,我们原是一个很兴旺的家族。我父母都死了,只留下光秃秃的风干的躯体。我父母在世时生得高大健美,风流潇洒,不瞒你说,他们是树中的美男靓女……我们不能像你们人类随便可以迁徙——不是批评你们,那是人类对土地的不忠,对祖先的背叛。 我:这大漠里,夏天烈日炎炎,冬天风雪酷寒,即使春和秋也是沙尘暴肆虐的时节;这里没有蝴蝶的爱恋,没有鸟儿的歌声,你们不感到寂苦吗? 树:这一切我们都习惯了。苦难、寂寞,我们不怕,我父母在世时告诉我:受苦受难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它可以净化灵魂,在苦难中获得新生。没有我们,沙漠真正成了死亡之海。我的父母,我们的家族都有过辉煌的历史。我的祖先就看见过班超和他的骑士,也看见过来往西域的商贾,他们的驼队还在我们身边歇息过,打过尖,晚上点燃篝火,围绕着我的祖先唱歌跳舞,度过一个寒冷的大漠之夜。我小时候还看见过成吉思汗的马队呢,成吉思汗,你知道吗?蒙古人的大英雄,他率领大军西征,就是从这里经过……实际上我们树的历史就是你们人类的历史。元朝有个诗人名叫马祖常,他不是你们汉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维吾尔族人,他写过一首诗:“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那时候,我们前面那条路上可繁忙呢,驼队、马帮,还有僧侣,征人,来来往往……如今路也被风沙淹没了,人影也不见了(老树伤心地叹了口气)。唉,我的日子也不多了,只要我还能绽出一片绿叶,我都要同风沙搏斗,坚守这里,守望着我们的家园。 我:你们守望家园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可惜,我们人类精神的家园没有了,我生活的那个世界,是金钱喧哗、权力肆虐、病毒蔓延的世界……人类的末日也要降临了。 树:那是你们人类的悲剧,是你们人类自我导演的,你们逃脱不了末日的审判。这和自然界自身的灾难不同,洪水、地震、火山爆发、沙尘暴……都给地球的一切生命带来苦难。由于你们人类的贪婪、自私、欲望的恶性膨胀,这些灾难越来越频繁了,我相信,终有一天,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我离开塔克拉玛干沙漠时,和胡杨林拍了好几张合影,悲壮的胡杨林永恒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去年春天,我在河西走廊采访,那是行驶在武威荒凉的大山沟壑中。那山呈铁锈色,没有树,没有草,枯焦、干瘦,那山是一个死亡的躯壳。汽车穿行在沟壑间,山谷里有一条河流,早已干枯,河岸上只留下刀刻般的水纹线,醒着一缕河水的记忆。河畔有一方平整的土地,一个小村庄坐落那里。我们看到这村庄时,已经成一片年轻的废墟,武威的朋友说,人都迁走了,属于生态迁徙。村舍全是没有房顶的土墙方阵,土筑的院落,空荡荡的弥漫着一片死亡的气息。当我的目光扫描一阵,却发现有两间土屋,门窗俱在。屋后有一棵白杨树,高高地,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我们跳下车,奔向那座土屋。令我们大为震惊,从土屋里走出一个老汉,像个幽灵似的,他头发花白,目光浑浊,吃力地打量着我们,一言不发。问起来,才知道,前几年政府动员他搬迁,他死也不愿离开这里,儿子、媳妇、孙子都走了,这两间土屋还有这个村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守着这村庄,守着这棵树,还有他放牧的一群瘦弱肮脏的羊——这简直是一个古老的童话。我问老人怎么吃饭,老人说,每隔半月二十天,他儿子就开着车给他送些干粮、面粉、水和蔬菜。他说,他和这山这河都有着血缘关系,小时候,山上有草,河里有鱼,夏天在河里抓过鱼,冬天在河上划过冰,现在河干了,草死了,山也死了……他眼睛里蕴含着悲怆,脸上是一片木然。老人又说,村里人都走了,我不走。他指着对面山坡说,那里有他的爷爷奶奶,爹和娘的坟——其实很难看得清,那坟堆和大山融在一起了。这土地是他们家族生活过的地方,有他的根,有他的神。 我倾听着老人的叙述,虽然方言味很浓,断断续续,语句不连贯,但我感到惊心动魄,有一种震撼灵魂的力量。这是人类最高贵的精神,人类就是凭着这种精神而生存。爱的力量比死亡更勇武百倍。 后来的事情,武威的朋友告诉我,那老人在去年冬天死了,是一个风雪天,老人为寻找一只走失的羊,从山上摔下来,死了。他儿子半个月后才找到他的尸首,用屋后那棵树做了一口棺材,把老人安葬在“祖坟”上——从此,这个村庄从地球上真正地消失了。老人用他的生命为这个村庄画下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句号。这消息,使我心情沉重,其实我和那位老人只有一面之交,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但一个巨大的命题却始终盘绕在我的脑海:人啊,你究竟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腾格里沙漠,回到马莲草身边。马莲草绽蕾了,开花了,倔强地挺立着,蓝得纯净,蓝得深沉,像天空,像海,在这荒凉和寂寞里,默默地生存,默默地繁衍。这小小花朵里,这纤弱的枝茎里,蕴藏着多少世俗的、冷漠的、庸浅的眼光无法诠释的生命意志和力量啊! 我心里萌发出一个伟大的主题:双手举起相机,颤抖着手指按下瞬间和永恒——这是世界上最辉煌的风景,这是羌笛哀怨、春风不度的腾格里生长出来的春天!感谢马莲草,感谢沙漠,感谢阳光,感谢风,感谢天地日月之精华,共同打造了生命的神圣和庄严,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经典! 这伟大的灵魂是虔诚的,面对炼狱般苦难,你是苦行僧,又是欢乐佛。而我们生活在富裕的城市和肥腴的土地上,心灵却那么浮躁、迷乱,灵魂那样荒芜和苍白。欲望之火已把城市烧成灰烬,人满为患,金钱肆虐,权力纵横,已使我们的日子长满霉菌;我们的生活已被看不见的竞争的魔爪撕得支离破碎,鲜血淋漓。 四月的阳光照耀着腾格里空旷的大漠,没有风,腾格里是一片苦涩的静默。这时,我感到彻骨的孤独,一种被遗弃的感怀,涌上心头,我的心酸酸的,只想掉泪。 3 腾格里沙漠虽然已有火车通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并没有彻底淘汰古老的沙漠之舟——骆驼。它们依然默默无闻地步履稳健心无旁骛地,跋涉在茫茫的风沙线上。高昂着头,微眯着眼,将信念和毅力,忠贞地写满重重叠叠的沙丘。 那是一个晨光初露的早晨,我漫步在沙丘间,大漠在粉红的霞光里变得温柔、迷人。沙质极为细腻,鎏上一层薄薄的霞光,犹如铜浇金铸般的高贵典雅。天空由黛蓝色变成瓦蓝,蓝晶晶的天,透明的空气,鲜丽的朝霞,使人感到大漠并不荒凉,沙丘波涛起伏,犹如奏响一曲无声的滂滂沛沛的乐章。 就在这时,我隐隐听到一声声驼铃——叮咚叮咚,从大漠深处传来,犹如深山里的泉韵,有一种寺院晨钟梵音般的庄严。 千里驼铃动朔方。我想起了古人的诗句。久违了,大漠的骆驼。 骆驼是大漠一页鲜活的历史,这些古丝绸之路的拓荒者的后裔们依然穿梭在这风沙线上。看见它们总想起古代和中世纪那波斯老贾或是汉唐的商人,赶着驼队,满载着波斯的玻璃、胡麻、苜蓿、葡萄干、绿豆、宝石等等,和从中原装载的锦帛绸缎、茶叶、陶瓷、铁器……长长的驼队跋涉在戈壁旷漠,缰绳联着缰绳,驼铃声伴着驼铃声,像一曲雄浑而又悲壮的慢板,奏响在风路浩浩沙路浩浩的天地间。炎炎烈日,萧萧风沙,骆驼和拉驼人已饥渴难忍,但他(它)们依然艰难地行进。骆驼高昂着头,微眯着眼,目光蕴含着信念,步履稳健,不急不躁,那种坚韧和毅力,那种雍容大度和充满自信力,使你会感到一种敬畏。这些伟大的独行者在传播着友谊和文化。一条古丝绸之路编织了几千年人间动人的故事和史诗。 骆驼是苦难的象征,是上帝派它们来到人间,与人类一起历经苦难的洗礼。诗人们把骆驼比做放逐者,放逐者自有放逐者的旷达,他决不屈就强加的忧患,更藐视令人窒息的浮华。这古老而荒凉的沙漠,留下它们深深的蹄窝,那是先哲的诗行,是特立独行伟大秉性的传记。 太阳湮灭在大漠中了。大漠梵天净土般的幽静,落日的余辉映照在沙丘上,犹如灵柩前熊熊燃烧的火烛。一枚生锈的古箭镞裸露在沙滩上,像古老的符咒和占卜,恐怖和肃穆伴着萧萧暮色的降临,大漠出现一种幽冥和恐怖的宗教氛围。沙丘上的沙蒿和梭梭草像魔鬼乍撒的毛发,在夜幕中恐怖而狞厉。风吹过,索索有声,像念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天地间寂然如梦。 孤独的驼队和孤独的商贾就地露宿。骆驼围成一座驼城,拉驼人就依偎骆驼温暖的怀抱里,喝上几口烧酒,吃上几块干巴的馕,便对着初升的新月,弹奏一支曲子,那凄清的胡琴的旋律,像神曲一样在月色里飞翔,像幽魂一样在大漠里游荡。 腾格里大漠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路。从咸阳出发的商贾驼队就是沿着萧关道,经灵武过中卫,进入腾格里,然后到达古凉州,再沿着河西走廊跋涉而去。我曾访过一位驼人的后代,他说他的先人就是“骆驼客”。赶着六七十匹到上百匹骆驼,最远到达过现在的阿富汗,伊拉克,往来一趟八九个月到一年。 他说:骆驼是天生受苦受难的角色,常常几天吃不上草,喝不上水。忍饥受寒,满载重负,却无怨无悔。骆驼食量大,一口气能吃六七十斤草,饮好几桶水。骆驼的食物都很粗糙,沙棘、索索、骆驼刺,很坚硬的枝叶,枝条上还长着满疙针,它用舌头一裹,全进了坚强的胃。 他说,骆驼最通人性,温厚笃实,对孩子妇女都不欺生,只要缰绳往下一抖,它那高大的身躯就很驯从地卧倒在地,让你骑在它的双峰间。风一程,沙一程,它会把你安安全全送到目的地。骆驼的记忆力很强,凡是它经过的地方,它能记住哪里有草,哪里有水,哪里适合拉驼人休息。它的嗅觉非常灵敏,能闻到几公里外的水草味。过去“骆驼客”骑上头驼,把后面的骆驼用缰绳连在一起,你尽可背依驼峰打磕睡,凭着节奏舒缓的驼铃声,你可以放心地让骆驼们走下去。 他说:现在虽然有了飞机、火车、汽车,有了高速公路,现代化交通工具很发达,但大沙漠里仍然离不开骆驼,这古老的牲口,伴随着人类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只要沙漠存在,它们仍然伴随着人们继续走下去。什么秦皇汉武,什么唐宗宋祖,说白了,是骆驼开辟了一条伟大的丝绸之路。 听罢年轻人的讲述,我对骆驼肃然起敬,骆驼被世俗称之为“四不像”,其实正是它集中许多动物的优点,才适应这艰危的生存环境和苦难而粗糙的岁月。它的脸型像猴,耳朵像牛,脊梁像龙,嘴巴像兔,大腿像鸡,鼻子像狗……几乎囊括人的十二属相。这十几种动物的灵魂铸造了沙漠的怪物,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助手。 我想起元代诗人马祖常的诗句: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 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 沙羊冰脂蜜脾白,个中饮酒声澌澌。 诗中的河西,就是指黄河以西地区,也就是今日的银川平原。沙羊,就是沙漠中的羊只,今称滩羊,宁夏五宝之一——滩羊皮,就出产于此。这首诗画出一幅宁夏一带浓郁的风俗画。那时,宁夏有招赘僧侣做丈夫的风俗,也反映出元代西域与内地经济贸易状况。 马祖常还有诗句:“橐驼驯象奴子骑”,橐驼即骆驼,那意思说连小孩也可以骑。 马祖常不是汉族人,他是“雍古特部”,即维吾尔族中的贵族。他曾在灵州一带生活过,对宁夏的风物地理十分熟悉,也对北国风光格外迷恋。他另一首著名诗篇《河湟书事二首》(其二),更生动地描写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拉骆驼的商贾跋涉大漠的形象:“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叮咚叮咚,远处的驼铃声更清晰了,也更动人了。一队浩浩荡荡的骆驼,首尾相衔,出现了一种古典诗词的意境,使人振奋,又让人悲凉。这时,太阳已高高升起,朝霞鲜丽得像一幅水彩画,阳光温柔的光芒照耀着辽阔空旷的大漠。重重叠叠的沙丘,波涛翻腾,无边无际。沙漠之舟,多么生动形象的比喻,一页驼舟,迎着风涛沙浪,行驶在漠漠天地之间。那声声驼铃,犹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悲怆雄浑的乐章演释着人类命运的蹇涩和苦难。 叮咚叮咚,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凋零了,后来的骆驼仍然记住了它们的道路。 扫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ry/8414.html
- 上一篇文章: 名家讲堂杨振铎等大家讲授杨式太极拳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