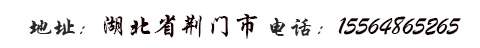难忘偷吃光饼味
|
作品欣赏 第期 难忘偷吃光饼味 吴慧英 从小,我就很贪吃。因为贪吃,我总爱偷吃。为了偷吃,我经常和父母斗智斗勇。家里的米缸是我觊觎的地方。大米可以拿到光饼铺换光饼,而光饼铺离我家才十几步,无疑是个有利的作案条件。害怕光饼铺老板泄露秘密,于是我拉来妹妹做同案犯——由我负责偷米,妹妹出门换饼。舀米时须得胆大心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床,而米缸就在父母的房间里。我仔细听着她的呼吸声,辨别母亲是否睡着,等着母亲发出均匀的轻鼾声,我就踮起脚尖,悄无声息地来到米缸旁。最难的动作在于舀米,舀米用的铁皮筒插到米堆里,总会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声响听在我紧张的耳中,无疑是巨大的声音。但真正的巨响是有时母亲醒来怒喝:“谁!干什么!”这不啻于惊雷炸响,吓得我丢下铁皮筒,几步就窜出母亲的房间,行动宣告失败。几次后,我就学乖了,改用手拨拉大米,动作轻柔如春风拂面,于是便只剩下大米被拨拉到塑料袋里的轻微声音,成功率大大增加。踮脚溜出父母的房间,我把“九死一生”得到的大米交到尚不知害怕的为何物的妹妹手里:“一半换没肉的,一半换有肉的。”换没肉的光饼,是为了先把肚子塞半饱;换有肉的,是为了解馋。如狼似虎地吃完没肉的光饼后,就进入有肉的光饼美妙滋味的享受阶段了。轻轻咬下一小口,酥脆的饼皮和鲜香的肉汁,混和着葱香、姜香、芝麻香,鲜美的滋味在味蕾里炸开,津液溢满整个口腔——我忽然深刻理解了刚学的成语“津津有味”。舌头卷起恨不能起舞,情不自禁地眯起眼睛——真香啊!香得我恨不能把舌头都吞下肚去。说起建瓯光饼,可大有来头。相传明嘉靖四十二年(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率军由浙入闽追击倭寇。行至闽北,连日阴雨,军中不便开伙,且兵贵神速,架锅烧饭会拖延不少时间。当地百姓便用面粉烤制出“金面、银边、瓜子咀”的小饼,中留小孔以麻绳串起背于肩上,小饼放置三五天都不失柔软有嚼劲。因为耐存放、易充饥、味道好、便于携带,小饼最终成为戚家军的军粮,因此称之为“光饼”,之后又衍生出了加入猪肉和葱、姜的光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缺油少荤匮乏副食品的年代里,偷吃成为我童年岁月里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令人口滴馋涎的光饼,是我幼小的心里无上的美味,有着贫困和物质缺乏的味道。而如今,在建瓯市——这个千年建州的城乡,光饼早已从儿时难以企及的“高堂”,走入千家万户的饭桌茶几、进入随手购买的纸袋里,成为随意品尝的点心或赠送亲友的特色小吃。我也不再需要偷来大米换光饼,光饼的味道从偷米时的紧张惶恐,到现在随心品尝的怡然自得,有着改革开放后物质极大丰富的味道——这是幸福的味道。作者吴慧英,建瓯人,南平市作家协会会员,简单的生活,简单的人。南平市作家协会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ry/9849.html
- 上一篇文章: 快观察丨洽洽多元化重创果冻等产品失败丢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