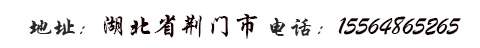记录的云上火把节
|
去年暑期,曾带侄儿回老家看父母,正逢火把节期间。时间一溜烟又到了今年火把节,翻看去年火把节第二天记录下来的文字,算是过了一次云上火把节。以下即是那些文字。 不少村子去年砍的树就没点成火把,本想着挨到今年火把节,疫情总该过去了。他们就耐下心来,照常生活作息,专等来年火把节,再加倍热闹一番。今年才到七月中旬,不少人已经摩拳擦掌,着手准备。往年扎火把卖的人家户,早早把扎成的大大小小的火把,拉到街上卖。几个年年竖大红火把的村子,开始安排人手扎火把。亲戚朋友也早早相约去看火把了。一切都朝着时间的指针期待着。 节前,政府部门也在公众显眼处贴了通知,仍就是叫大家节日期间保持警惕,做好防控。结合往常,大家的理解,那也就是公家做个姿态,只要不亲自来人根究,或者电话要求,一切还可照旧。 人们各自忙碌着,多数人在筹办节日吃食。火把节必备的炒豆啦,时令的菌子啦、鸡鸭鱼肉之类都已就绪。做生意的,买把稍大的火把准备着,有小孩的人家,也按娃娃大小身高,量身扎好或者买好了火把。性急的,还把花红、苹果、梨、香蕉这些点火把前要挂的水果,早早拴上线,一层层一台台地挂到火把上了。大火把尖上的斗、梆、升也准备就绪,炮仗、烟花、钻天鼠也支在了火把旁边。用来招待迎候看火把亲戚朋友的方桌、小凳、果碟、酒水一应准备齐全。只待过节这天,晚饭后,天一擦黑就点上火把。女人们围着火把跳舞、男人们围桌喝酒聊天、娃儿们放烟花炮仗疯跑。是啊,沉闷时间长了,是得烧一烧炸一炸乐一乐了。等着把,只有那么两三日了。 火把节头天早上,母亲散步回来,对家人说:我听羊毛村的人说了,上边呢喊他们说今年也不准他们村竖大火把了。哎,只可惜了那棵大树了,支在路边上都一年多了,到明年麽怕是要朽掉了! 外孙说:阿婆,怕是准竖呢怕,前晚我跟姨妈走路到秀邑村口,还见着他们呢大火把呢,头头都用塑料布包起啰,怕是都已经扎好了。 外婆:那你们到时候就去秀邑村瞧得了,大老远回来一趟也不容易。 其他人说:不准点嘛肯定到处都不准了,秀邑也不会点了,哪个敢冒这种险,要担责呢。听说这几天南京疫情老火了,全国好多地方又紧张起来了。还在说这几天来丽江玩呢人,扫健康吗,出了好些“黄码”了。 公家不准集会,但老百姓呢浓情不减,该吃还要吃,该乐还要乐一下。娘家接姑娘女婿,鱼肉酒水俱全。自家门前的火把,天黑了要给娃娃们点上。不点火把的人家,早早吃完晚饭,走路兼看热闹,朝往年火把节热闹去处去走走看看。 城西园的人出门,自然朝南往城的方向走。 先从环城北路一直向西走,过花树村。左右各有一家店铺门口放了火把,东头北行这家是KTV店,几个男店员在火把旁抽烟;西头南行是个火锅店,几位女士正在旁边桌子上摆炒豆、水果。过十字路,医院门口,还有一坝田就到秀邑村了。往年,医院前边那个十字路口,就看得见秀邑村的大火把了,还听得见响亮的、女人们围着火把跳舞的音乐声。今年一直往西走,都与平日差不多。村口,用于竖大火把的树还躺在路边,前几天树梢上护着火把的塑料布被揭去,扎好的火把也拆掉了。场上,几个年轻后生,停了摩托,散淡地用白族话聊着。看来他们对今晚不能看热闹、看美女,亦或偶遇一位心仪呢姑娘有些沮丧。场地北边不远,一群妇女同往常一样,开着小音箱,跳她们的广场舞。看来对于不准点大火把,她们早已知晓。 继续沿建设路往南边走,过鹤阳路交叉口,一遛的铺子和人家户,并无点火把迹象。再前,建设路与学府路岔口,西边南行上倒有了一个火把。约有两米高,已经点燃,几个人在路边铺着炮仗准备放,背后是个新开不久的百货店,几个男人在门口方桌边坐着闲聊,桌上摆了几盘水果、瓜子、炒豆。 再沿建设路向南,左边新建的高楼小区,自然没人点火把,一个成都火锅店放着响亮的音乐,从门窗看进去,似无几个食客。远处,右前方黄龙潭边,一排餐饮店,门头灯光耀眼,照出很远,同样放着震天价响的音乐。再远,谷堆山迎风山后边,那个山凹平台工地上,放着烟花。先见花开,久后才听到爆炸声,离这儿已经不近了。 走到建设路尽头,隔着绿油油、正抽穗孕穗的稻田,可环看周边村庄——上庄、迎邑、和邑、小教场、姜官屯,有人家你方唱吧我登场地放着烟花,但都不多,一村也就那么两三家在放,不算热闹。 从黄龙路往城里方向走,来到十字路姜官屯村岔口,我和侄儿决定拐进村口看一看。“姜官屯”字样大石头下,一个烧香炉子,几位老妇在烧着香。排场中等,不像独家独户来烧,看样子是算村集体烧节庆香。前边,灯光亮堂,路右棚架下石凳上,坐着些中老年男士,聊着看着。前边宽处,音乐声中,中青年妇女正跳舞。我们走过去,还未细看就理,从左边凳子上涌上来几位女士,一人端了一盆炒货、一人端一盘糖果。边说边往我们每个手上舀来一大碗瓜子、一人几颗糖:来来来,阿妹、小弟,吃瓜子吃糖。我们手捧着吃食,嘴里不停地说:够了够了,拿不下了。舀瓜子的才止住。 我看没有火把,只旁边一个容器里烧了一堆火。问道:今年也不准点火把? 答:是喽嘛,不准点。 我:是是,疫情防控。你们这样娱乐一哈也得了。 手捧瓜子,再走尴尬,便退了回来。 续朝城里方向返回。过文庙公园,感觉还无平时热闹,便没进去。公园路对面,北桥头村这边有一家的火把正烧着,只这一把而已。 从南大街一直到钟鼓楼,沿街的商铺,火把全无。钟鼓楼东南角商铺前,卖火把的还在卖,但大人们领着的娃娃,只买些小炮仗、钻天鼠之类。钟鼓楼在夜晚的灯光照射下倒是别有风味。 从钟鼓楼到县政府,自古叫做“府门前”这一段,仅西门街口北边一家商户点着个火把,主人邀约着几个朋友在旁边烤东西吃。 “北门前”一段,拢共西行上两个火把,丁字路口那家已快燃尽。中断那家剩下三分之一。这条还保有古旧气息的北门街,街灯暗淡,也没什么瞧场了。约了侄儿折返,还是要从钟鼓楼向西看看。 钟鼓楼所在这条路似乎叫做鹤阳路,临街都是些商铺。那么其西头该是鹤阳西路了。这一条路两边倒有几户人家门口点得有火把。各家铺子的灯辉映着街灯和树影,娃娃在火把旁边放钻天鼠,大人们或照管火把;或围火把边桌旁,吃酒、嗑瓜子、削水果、冲壳子(聊天)。这是今夜节日气氛最浓的一段街区。 再沿鹤阳西路过西,日月广场处人头攒动,上演着近年火把节都有的大戏。孔明灯是台柱子,各色人等、吃喝杂耍都陪衬着灯。小娃娃在充气大塑料盆中钓鱼,中娃娃在烧烤摊前忙吃,大娃娃和大人都在忙着买、放孔明灯。从地面到天空,满是错错落落红彤彤的孔明灯。感觉所有在这广场中的人都已乐而忘记时间,忘了一切,只为孔明灯捧场。 小菜市场西门口那家超市也点着个火把,几个人在旁边桌上冷一筷热一筷地吃着,路人走过,强如未见(超市地处菜市场门口,他们天天看的人多了去了)。 花树村口的那几个火把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过东,往年都在门口点火把的映秀嬢家,今年没见点。从环城北路转向城西园村道,就可看见狮子门前右边的周四代家点着火把。待我们走近,看清桌边坐着四代爷孙、四代父母,还有两个朋友。热情地叫我们坐一下,递过来吃货。往北看,木匠徐灿云家门口也点着火把。 后记:老家在滇西北小县城,那里的民众多为白族,像我们这种不是白族的,倒成了该地的“少数民族”。所以,日常生活习惯,节庆风俗什么的,早已被白族同化。坝子里过的火把节,除了居于甸南坝漾弓江东岸的为数不多几个村庄,据说祖上是从四川地方搬迁过来,到目前他们的口音里还带有川音,被当地人称作客家人的,是在农历六月二十四过火把节,县城和其他村庄,自然是过六月二十五的白族火把节。白族火把节是有些传说、来头和仪式感的。 民间广泛流传的起源是“火烧松明楼”的故事。相传在唐代,大理地区六诏之一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企图吞并其他五诏。六月二十四这天,皮逻阁诱召各诏首领到松明楼喝酒,纵火将他们烧死。邓赕诏主的柏洁夫人早就看穿皮罗阁的野心,劝丈夫不要去,但迫于祭祖和南诏的威力,不得不去。柏节夫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于是将一只铁钏戴在丈夫手上,后据此认出了丈夫的遗体。南诏王见柏节夫人貌美聪慧,便逼她为妾。柏节夫人假意答应,但回去将丈夫掩埋后,率众与围城的南诏兵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后于六月二十五日投海而死。 每到六月二十五这天,大理、剑川、洱源等白族聚居区民众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杀猪宰羊,庆祝节日。人们在村寨广场中央,用一根20来米高的木杆竖在地上,周围用麦秆、干柴等捆成一个大火把,上面插着预示五谷丰登的彩色升斗,一根根彩线串起的梨果挂满火把。以此来纪念高风亮节、坚贞不屈的柏节夫人。 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火把节前父亲不知为啥心情大好(那时他被错处回乡务农),早早就劈好了大小长短不一的一堆松柴,扎了一把一米多高,堪比工艺品的精致火把——我父亲年少时,正遇上他经商做生意的父亲主持建盖私宅,三枋一照壁的房子。来自坝子里校场坝北面,波南河村的木匠师傅兄弟两,被称为高大师高二师带领的一群工匠,在父亲家工作了三年。期间我父亲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木工活计,还把做木匠活当作了一种爱好。虽然他后来求学、从军、从教、务农、再从教,但还一直保留着他的一整套木工工具,包括木马、锛子、推刨、凿子、墨斗、墨线等等。他也做了一些自用的家具,高矮八仙桌、椅子凳子什么的。所以他扎的火把,就有那么几分像个工艺品。削了皮的白白净净松木片,围圆了一台一台逐渐缩小了往上搭,每一台还挂了些桃梨果子花红什么的,顶上挑个绿植尖儿,再别上几面小彩旗,一把漂亮火把就巍然挺立在了院心里。 终于到了火把节这天,也终于等来了黄昏,我们连蹦带跳簇拥着父亲把火把扛到了大门口。星星出来了,火把点上了。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巷子的中部,没有路灯的年代,火把的光焰照亮了大半个巷子。火把顶上的光,在烧燃松明的哔哔啵啵声中,射向遥远的星空。当时,比我们大的孩子说,按照物理上的算法,天上最亮的那几颗星星,在四十年后,可以看到今晚我们火把送去的光亮。然后我就开始算,那是什么时候,那时我有多大,在干什么?还有,那颗星上如果有人,他们也会回应我们一个光束吗?还有......那正是小孩子喜欢各种幻想的年龄。 火把刚烧去最顶上的两台,巷子东头过来了几个移动的火把。走近了,是小队(那时村民小组)的一位领导带着几个社员,人手一把火把。有烧矮了端着的,有刚烧了点尖儿扛着的,还有尚未点火的。队领导急急的对父亲说:赶快赶快,扛起火把,到谷田里去秋(“熏”意的方言)蚊子!父亲见状,也没多问,扛上火把就跟去了。我们急得跺脚:我们手索还没烧掉呢!大人们说,快拿过来,我们到田埂子上一起烧。 那夜后来的事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估计是母亲劝慰了我们姊妹几个,后来就进屋睡觉去了。父亲应该回来的很晚,我们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才见他,也忘记问昨晚何为了。 那之后,随着年岁渐长,逢火把节偶尔想起那晚的事,也有疑惑:拿火把到谷田边秋文字,难道谷子也怕蚊子叮的吗?再后来,又想:久远以前的火把节,人们有成群结队举着火把到田间地头,向火把撒松香粉,给谷物照穗,是消除病虫保丰收之意。那时候的队领导,也是上过学开过蒙,识得几个字认得一些古理的人。如果从这个层面想,在那样的年月,他也只好以“秋蚊子”为借口去为收成祈福了;还有,那时水稻普遍栽有红谷和白谷两大类,当地有种说法,如果当年火把火焰呈白色,则秋收时白谷好,若火焰翻红色,那就红谷好。那些壮年男士们,定要举着火把到田埂上照它一照,看看秋收时节何种谷子收成好;还有一点,趁此机会,一群大男人,黑夜里,人手一把火把,撒丫子在天幕下,大地间的田埂上跑一跑、疯一疯,在那个憋屈久了的年代,难道不是一件畅快淋漓的事吗? 在我们幼小时候,老家很少有集体竖大火把的,但私人家里点个火把较常见。到晚间,沿着县城北门外,朝:“北门前”、“三步卡”、“府门前”,一直到后街、南大街,隔个一两家,就可以见到这家门口点着一把火把。火把旁边,常常设着个小方桌,桌上摆着桃梨果子和炒蚕豆,桌边放几个小板凳。见熟人逛到近旁,就盛情相邀,坐一坐,聊一聊。有些热情的人家户,即便不是熟人,走近前来欣赏自家的火把,也要寒暄几句,抓来炒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环境条件一天好过一天,人们也激情渐起,各村寨扎大火把,私人家请客吃饭也就普遍了。只是那时的我们,虽不算太爱学习,但总规案头上是有作业要完成的。再后来,家乡的火把节,多数时候成为遥想。 火把节吃的方面,现在可以杀鸡宰羊吃大餐,我们小时可不这样。常常是:煮面条吃,野生菌子做哨子。以至于好多年我都以为,自古以来火把节的晚餐就是吃面条的。为何如此——那时的农村,田里产出的,基本跟不上人嘴需要吃的,常常是这边还没收上来,那边早已等着下锅了。夏天,村民的米缸早空了,眼巴巴等着干地麦子收了,小队领导急忙领着大伙收打,分到各家。大家就忙忙地淘麦子、晒麦子、排队磨面。面背回来,就赶快炕粑粑给娃娃们吃了。没吃几顿,就没了——干地本来就少得可怜,那就是西山脚下坟地开出来的一片瘦地而已!就又赶快收打刚刚成熟的水田麦子。水田麦子就相对多一些了。这时的村民,除了收工后炕粑粑给娃娃吃,还可以安排娃娃们,白天端一小盆面粉,到“北门前”的擀面铺里擀面了。晚饭便可以改善成面条了。至于哨子,家里有啥是啥,莴笋叶啦、茴香尖了,再不济,几个盐豆啦。我们家的哨子比隔壁邻居要多一个品种:菌子。我有个小姨嫁到朝霞寺下的和邑村,他们村山清水秀背靠朝霞山。雨季到来,雷声一响,野生菌就在山里冒出头来。整个菌季,小姨父天天半夜三更起床进山搜菌子。然后在工余,他们夫妇两轮流背着菌子到城里来卖。晚饭前,我们家就常常受到他们给来的一份菌子,青头菌、见手青、或者其他杂菌。我们就把它拣洗好了,待父母回来,下锅一炒,面条熟了就浇在上面,吃的很香。到了火把节这天,母亲就狠狠心,多切上一点腊油,那天的面条吃起来就更香。 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老乡加朋友,那段时间她家小孩有些不省心。我两就联合起来做小孩的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对我们有着相似经历的小时候的忆苦思甜。什么菌子面条啦、什么想改善伙食还要自己下河去捉鱼摸虾啦、要吃水果还得上树去摘梨偷瓜这一类。本想让他感觉到他们现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童年,不成想他听完后拍手说:哇,你们小时候也太好玩了嘛,可以捉鱼摸虾玩泥巴,上树摘梨偷瓜!还有你们吃的,多生态呀,自己的麦子、自家的面粉擀的面,还天天可以吃野生菌!听得我两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我两对视,无言中对方心里的话却心知肚明——我们小时候,真的挺幸福的呢! 以上就是我今年过的云上火把节,也算别有风味吧!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yx/10078.html
- 上一篇文章: 二手车行业收缩抗疫优信降薪瓜子大搜车裁
- 下一篇文章: 尸身不腐震撼一时,是执念不散还是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