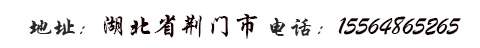散文抗疫尚未成功,瓜子仍需努力
|
举凡中国人,没有不嗑瓜子的。 今年突然“抗疫”,正月十五过完了,人们还得窝在家里。 “瓜子”就没结束使命。这个其貌不扬、在年节期间出镜率堪称最高者之一的小零食,能让不同的人嗑出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概念,甚至不同的寓意。 瓜子,顾名思义。不过,您要统称所有瓜的籽为“瓜子”,肯定会有歧义。如今,“瓜子”似乎专指葵花籽,其他瓜子一定要冠上瓜名。有时候,我的确有些相信父亲曾说过的“瓜子是洋人用来麻痹中国人的东西”。向日葵起源于美洲,传入我国几百年的时间,它就轻而易举地击败众多传统零食,一跃成了中国人最主要的干果之一。但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中国人“洋为中用”和“好学进取”。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嗑瓜子的水平已达到所向披靡的程度了。不是我故意贬低外国人,记得早些年看过罗马尼亚电影《神秘的黄玫瑰》,故事情节已记不清,但那位神秘大侠马背行囊里总装满葵花籽和咬瓜子的镜头始终不能从我脑海里抹去。一个大侠嗑瓜子技巧还不如中国一个小孩,欧洲人的水平肯定也高不到哪去。俄罗斯人吃瓜子很特别,他们总是直接将一把瓜子仍进嘴里,然后连皮带肉吐出一堆,这种“猪八戒吃人参果”式的吃法,根本谈不上是“嗑”或“品”了。而在葵花籽的故乡,美洲人根本不吃带壳的葵花籽;日本人不仅不吃瓜子,还用葵花籽喂仓鼠……如此看来,瓜子落户中国算是找对了地方。在中国,过上“花样年华”的生活,是葵花籽的幸运,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荣耀啊。 丰子恺在《吃瓜子》一文中对“瓜子”的定见,提出了不少可供追寻和反思的角度,也让现代人重新思考“瓜子文化”究竟有没有缺陷。他说:“中国人显备三种博士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和吃瓜子博士。”现在看来,“吹煤头纸博士”是有时间设定的,而“拿筷子”无需赘言;可“吃瓜子博士”确实有些冤。事实上,中国人吃瓜类籽的历史非常悠久,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辛追夫人的肠胃里就发现“甜瓜子”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瓜熟爆裂取仁,生熟、炒熟俱佳”。可以说,“瓜子”通过与“嘴巴”多年的磨合,最后以“炒”的形式满足人们需求,称得上是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 “瓜子”这种既不能饱肚,又浪费时间、生产垃圾,还易让人口渴的干货零食,让人嗑在嘴里的同时,投射到其身上的还有“炒”的因素,我们不正处在一个炒作的时代吗? 不过今年这种特殊时期,普通人安安稳稳待在家里,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了。 诸位“吃瓜子”仍需努力啊!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fb/9963.html
- 上一篇文章: 为什么美国对马王堆女尸那么上心,甚至愿用月球土壤换取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