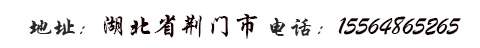姨父
|
中药治疗白癜风方子 http://baidianfeng.39.net/a_wh/151230/4752063.html从小到大,每年春节的时候,年初二那天都是到大姨家集合聚餐,饭后时间家人们坐在一起抽烟喝茶或嗑瓜子儿聊天。姨父烟酒不沾,喝茶会拉肚子,瓜子花生这些零食我几乎没见他碰过。不过席间姨父照样能在亲戚们的推杯换盏间聊得火热,并且见缝插针般用端庄板正的姿态以及认真的表情把每一口饭吃完。饭后的家庭群聊姨父很少能有机会参与,因为每年都有好多已经毕业的学生来拜年,有次还碰到过一位快五十岁的学生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姨父每次都是在书房里跟他们促膝长谈,学生们坐得各有各的歪歪扭扭,对面姨父永远笔挺如军姿,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说到激动处偶尔抬起来挥舞两下。脚上穿着家里的旧棉拖鞋,裤管往上提溜着,露出一截被袜子包住的毛裤。姨父是位初中语文老师,兼职务农,但在我们全家人眼里,姨父是一本行走的博物大百科,有花草野果不认识,去问姨父。有生僻字不认识,字典上也查不到,去问姨父。见到了什么新鲜器具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去问姨父。甚至捡到块奇怪石头都要拿去让姨父鉴定下,看看是不是文物或宝石。我来上海工作前,每年春夏经常一大家人一起去爬山,每次这种时候我都很怕跟姨父走在一起,因为姨父知道的典故实在太多,不管看到什么都能讲出一堆名堂,一草一木,在他眼里都是学问,总也讲不完。比如说去大基山或文峰山,姨父能把山上的每块摩崖石刻讲上半小时,从书法品评讲到文物保护。我只贪玩,听不进去,总想着找机会逃掉,听了那么多年除了那些石刻是郑道昭写的,别的什么也没记住。所有家庭聚会或结伴出游的照片几乎都是姨父拍的,他自己的照片却很少,翻看照片时姨父经常会说,有别人的照片就证明这里他到过了。 姨父和小时候的我,在云峰山顶 初中时有一年,姨父在学生作文里看到市东某村有座山,人迹罕至,当地村民称其为窟窿山。后面找了个周末就带上全家捎上我出发去寻这座山了。骑自行车小半天,一路上不停的打听才找到,结果就是光秃秃的几个小山包。风景没什么看头但不妨碍一家人自娱自乐。我们爬上了最近的一个山顶,抬头看到旁边稍高山头上也有几个人,也正在往我们这边看。姨父靠过来小声跟我说,“他们往咱这儿俯视,心里肯定才自豪呢!”我听完哈哈大笑了几声,又觉得不过瘾,两手拢成喇叭对着山下“啊啊”大喊。对面山顶的人听我喊完,也开始喊了起来。于是两边山头像比赛一样,一边一声的啊啊叫着,都努力让自己这边声音更大些尾音拖得更久些。姨父一直在旁边笑眯眯的看我们瞎闹没有参与,对面山头嗓门实在太大,我们喊输了又不服气,于是我跟嫂子一起撺掇着姨父出马。姨父先是调了下气息,调的有点久,我跟嫂子都以为是他不想瞎闹没搭理我们,就在我想再开口央求的时候,姨父突然喊了出来,或者说是唱更合适。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啊啊啊不算破坏规则,但声音嘹亮,调子古朴悠扬百转千回。姨父一声唱完,两山俱寂,清风徐来。片刻后我回过神来跟嫂子说对面被镇住了,姨父在旁边笑得含蓄又得意。也是那天,姨父给我和侄子看山上小虫子做的抓蚂蚁的流沙坑,我跟侄子吵着要看小虫子长什么样,姨父有点不忍心,说它做这样一个坑要花好久好久的功夫。但经不住我们缠磨还是找了根小树枝,小心又利落的把小虫子挑了出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蚁狮。之后,姨父又用树枝把它小心的引回了之前的坑里。大概是我上初中开始,亲戚圈里开始流行钓鱼,有时候是搭车去海边钓,大部分时间是去离家更近的水库钓,传说赵匡胤曾经在那里饮过马,因此得名饮马池。经常周末我爸带我去水库,去了就能在岸边见到姨父。每次姨父甩杆时,都会背朝水库扎好马步,回头几次确认方向,鱼竿擎过脑门笔直的向后甩去,样子有些滑稽,偏偏表情又是极其的认真。每次甩杆时岸边所有人都会停下手里的事情看姨父表演。后来姨父在岸边发现了一处秘密基地,要绕很远的路穿过大片的农田和树丛,小路尽头是整块黄色沙石形成的小小凸崖伸进水中,石边风摇岸柳石上浓荫覆地,石缝中细碎的野花和山椒草上有斑驳的日影跳跃。抬眼整片湖光尽收眼底,仿佛耳中的鸟鸣蝉嘶也是安静的。此后,姨父的反身甩杆表演就只在秘密基地中,有我和侄子两个观众。有一年夏天雨水多,大姨家村前干了十几年的南阳河又有了水,水深及膝,听说饮马池水库里有鱼游了过来。我跟侄子缠着姨父带我们去捞鱼,姨父也没推辞,找了根带长棍的那种小鱼网就下河了。河里果然有鱼,个头还不算小,排成一条线游着。姨父拼刺刀一样的动作拿着网子捞来捞去,当时七八岁的侄子觉得好玩跟在后面空手模仿他。捞了半天把这段河里的鱼都搅和走了,三人心满意足的空手而归。我上高中时姨父退休了,从此闲云野鹤。在家看书写字画画弹琴吹笛或是骑自行车出去转悠。去的很多都是很远但又风景秀美的荒僻处。有一次带回了从山野间采的大把覆盆子,我跟侄子吃的时候姨父不出意料的在旁边叨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各处能骑到的乡野逛完了,又开始在市里逛,逛了几个月回来自己手绘了一张路网图铺在写字台上。后来还在姨父的写字台上见过自制的日历和手抄的《锦瑟》。有段时间市东在修高速路,姨父每天骑车去围观。回来后还会很认真的跟我们讲解各个施工步骤,大舅一直开玩笑说姨父是去监工的,风雨不误。那段时间去大姨家,只要姨父不在,大舅就会说,肯定又去视察高速路进度去了。退休后姨父在南平房里辟出一个小房间,倒腾他的各种创作,用贝壳粘的台灯,滑石雕的各种器物,树根雕的拐杖,木工家具,石刻印章…………后来大姨家建了新房姨父直接征用了屋顶阁楼做他的工作室,我上去看过几次,设备又添置了不少。我爱围观大舅干活,却不爱看姨父做事,因为姨父只会埋头苦干,又太过于认真,会很无趣。所以虽然对姨父倒腾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奇,我却几乎没见过它们的制作过程。有几件作品姨父几次要送我,我很喜欢但上海家里实在太局促没有地方放,就都一直没有收。有一次姨父雕的一枚滑石球体积不大我便带回了上海摆在家中,姨父知道了竟甚是欢喜。还有一段时间,姨父热衷于研究菜谱,尝试用黄瓜和苹果切细丝同拌,是浓浓的哈密瓜味道。做过一次后大家好评如潮,于是每次聚餐姨父都要亲自操刀这道菜。有次闲聊还听到他跟我爸认真的讲解做这道菜用小国光苹果口感最好,只是小国光因为卖不上价几乎已经被砍光绝种了。还有几次,姨父做了西红柿炒鸡蛋,说是比例搭配得好会有螃蟹的味道,只是试了太多次都没成功,后来就放弃了。姨父对菜谱的研究大姨不太买账,经常会在姨父讲的起兴时揭他的老底,比如全村人都知道的姨父结婚前每餐用两根筷子隔水架着一个馒头,熥熟了吃。大学暑假时,有一年跟着姥姥在大姨家住。我带了几本小说回去,问姨父要不要看。姨父说他现在越来越懒了,别说长篇,文章都很少看,每天就看看诗词,有时候诗词也觉得长,就只看下对联或者灯谜。我随手挑了本贾平凹的《废都》递给他,姨父也还是接了,拖在手上摩挲了一会儿就带回了书房。于是后面几乎整个暑假,姨父没事的时候就在他的书桌前看这本书。我自己看小说向来是马桶上坐着或者床上歪着躺着的,每次看姨父那样捧着本“闲书”正襟危坐我都觉得哪里不对劲很想笑,觉得姨父手里捧着的应该是《论语》或者《楚辞》之类的才对,有点像是我把一个好学生给带坏了的感觉。后来姨父还书给我,我总觉得经过一个暑假的翻看,那本书比我借出去的时候还平整了些。大二还是大三暑假时大姨家村里的小水塘里发现了龙虾,而且还不少,村里老老少少们茶余饭后多了项娱乐活动。我回去听说后就央着姨父带我去钓,姨父从前晚剩的菜盘里抠了根鸡爪子出来,拴在一条线绳上就带我去了水塘。鸡爪放下水后等了好久好久,旁边一位老大爷五六只都钓上来了,我们这边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到了午饭时间旁边的人都陆陆续续回家了,我们还是没有任何收获,老大爷还打趣我们说,他要是有根鸡爪子还不知道要钓到多少呢。他刚说完就有一只龙虾抱住鸡爪被姨父拎了上来,姨父笑呵呵的跟老大爷说这下总算可以交差了。过了好几年,我才反应过来,姨父当时说的交差对象是我。后来家里有啃完的骨头之类的钓饵时又缠着姨父去过几次,都比第一次要顺利,于是姨父也不再那么紧张认真全神贯注了,中间问我还记不记得鲁迅写过的,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高一同桌曾是姨父的学生,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上姨父的课,几乎整节课都在讲故事,故事很吸引人他很爱听,但考点从不会落下。高三同桌初中也是在姨父学校读的,但没跟姨父上过课,她跟我说很羡慕姨父的学生,还说毕业时,姨父送了他带的班上每位学生一副自己的字画,字画里都会写上是为某某学生作。她说好几个邻班好友拿着姨父的字画给她看过,她也特别想要。这样的字画我也收到过,而且收了好大一堆。大学某个寒假翻出来展示给发小二健看,二健说很喜欢,她也想要。姨父听说后就给二健写了一张,只是我妈带回家时路上风太大,没拿好一不小心撕裂了一块。我跟二健说下次一起去我大姨家的时候跟姨父再要一张。后来一起过去玩的时候我跟姨父说这事,姨父翻出了几乎他手头存的所有的字画给二健看,并在一旁认真的讲解:有几副写得特别好的,不是他的,是他二哥的字。姨父的二哥我也见过一面有些印象,不在本市住,也是位中学语文老师,人很清瘦,听大姨说学生们给他起了外号叫“骨骼”。二健选了姨父二哥一张字,是临的某位名家写的“道无极”三字。是哪位名家姨父当时讲过,我记不得了。选好后姨父熟练小心得将字卷起,严严实实的包好递给二健。后来回家时二健一路欢欢喜喜的紧抓在手里。记得之前印象里,姨父书房墙上挂满了胡琴,笛子,琵琶什么的,姨父能说出很多名堂,但我都没记住,所以也分辨不出到底是什么琴什么笛子。小时候经常好奇缠着姨父演奏,每次姨父都会答应,都是我听不懂也不爱听的曲子,往往听到一半就会跑走。我上初中那会儿,姨父还自己用硬纸筒刷了油,烫出孔洞做了支笛子,后来见我喜欢就送给了我。迄今为止,我也再没见到过比这支更漂亮的笛子。墙上除了乐器还挂有一些字画,之前听姥爷说,有一年他看到了一份国画挂历,觉得姨父会喜欢就带了一份回来,姨父见到果然欢喜得紧,用完也舍不得扔,仔细的把画裁下来裱框挂在家里。这事儿离现在大概也有三十年了吧。我现在还记得大姨家里,曾经有一张挂历上裁下来的画是一位披着蓑笠的老翁独自在风雨中走着。大概是我上初中那会儿,墙上的画和乐器都被姨父取下收了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想过要问。我跟大姨都很脱线。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商量着要结伴出去一边捡破烂卖钱一边周游世界。姨父在一旁不停的跟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说这事儿不可行。我跟大姨都没理他,热火朝天的研究我们的捡破烂计划。姨父从头到尾无力又执着的劝说被我们当成了背景音。直到大姨要起身去买装破烂及代步用的人力三轮车前一秒,仿佛魔法消失了一般,两人对这事突然又都没了兴趣,决定放弃。姨父在旁边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并且又继续摆事实讲道理,继续花了好长时间证明我们之前的想法是多么不周全。我跟大姨又忙着捣鼓别的去了,根本没听,只留姨父独自在那里一板一眼的苦口婆心。还有一次我想起大学旁边有家川菜馆做的瓦罐焖烧肉很好吃,于是撺掇着大姨一起动手尝试。先是去大舅家搜刮了一只旧粗陶罐,又拉来姨父当顾问。院子里架起一堆枯枝便点火烹饪。姨父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我跟大姨还有姥姥都只是流着哈喇子闷头捣鼓,没人真的听。姨父由于也没经验就没继续劝下去,最后,肉煮熟了坛子也煮裂了,没达到闷烧的效果。后来吃饭时,大家都浅尝辄止,只有姨父在卖力的吃,一边痛苦的吃一边认真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最终也还是觉得太腻吃不下去几块。后来我就到上海工作了,每年回家的时间很少,回去时听大姨讲,她和姨父一起推着姥姥去很远的地方接山泉水,初春看杏花,撸柳绒,路上遇到下坡大姨起兴踩在姥姥轮椅后滑下去,姨父跟在旁边小跑着护航。每次听到我都很是羡慕,约好下次带我一起去又每次都没有假期无法成行。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冬天厨房里生炉子了姨父就开始烤地瓜,认真的根据每块地瓜的大小计时翻面,并且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改进。此后每年春节回家都能吃到火候恰到好处的烤地瓜。吃的时候姨父会在旁边认真分析地瓜的品种特性,哪里烤得好,哪里还不足。大家都不太在意去听,都会点头夸赞烤得好吃。姨父分析完听着大家夸赞就会笑得很开心,表情自豪中带着一点点微不可察的羞涩。几年前春节假时看到姨父难得有这种坐姿,就用手机拍了下来大概十年前,村里就没地可耕种了,四五年前,姨父开始在村南的野地里开荒,翻捡出来的石头在地旁堆了一个小山。地里种了好多瓜菜,第一年浇水困难,收成不太好。年末姨父说他找到了诀窍,可以保证明年地里不管旱涝都能丰收。至于是什么窍门,大家都没兴趣,于是也没人追问,姨父就也没找到机会讲出来。后来果然每年都是大丰收,有一次侄子和侄媳来上海玩,车子后备箱里装了几个大麻袋瓜果菜蔬——大姨直接让他们把姨父的二亩地都运来了给我。前年夏末回家,刚好赶上姨父种的甜瓜收获,超大的个头,很甜,很面,吃的稍大口些就会被噎住,要捶胸灌水的折腾半天。那几天每次去,都要在大姨的热情劝说下小心翼翼的吃一大块。今年秋天,看大哥发的视频,姨父地里收的地瓜比脸大。姨父在开荒,小时候的刘咩咩看到姨姥爷翻整的土地忍不住想上去踩一踩之前读《西游记》时只记住了一段话,是一位樵夫的歌:“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虽然做的事情不一样,也没有歌里那么的出世,但我觉得这段写的就是姨父。每个平淡庸碌的日子,姨父都能自得其乐,过得神仙一样。一个月前,姨父突然得急病去世了。我想,他是回去做神仙了吧。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ry/6120.html
- 上一篇文章: 烟草局急报专供香烟黄金叶百年浓香细支
- 下一篇文章: 我的名字叫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