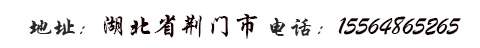古代的ldquo吃瓜群众rdquo
|
我国古代瓜业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时代北方瓜业比较兴盛,在上古文献中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印迹。秦汉至隋唐时期,南北共同发展,甜瓜、瓠瓜、冬瓜、越瓜的种植比较兴盛,种植技术明显提高,品种信息急剧增加。五代、宋元以来,西瓜、丝瓜、南瓜等相继传入并迅猛发展,黄瓜的种植、食用明显改进,我们传统瓜业的品种结构基本形成。甜瓜、瓠、冬瓜、越瓜、哈密瓜五种本土原有瓜种,黄瓜、西瓜、丝瓜、南瓜四种外来物种在历史上相继出现,不断丰富我国瓜业资源,构成了我国瓜业演进拓展的生动历史。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类型多样,境内绝大部分地区都适宜瓜类作物的生长,瓜的栽培历史极其悠久,种质资源十分丰富,形成独特的栽培品种体系,出现了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用途的品种类型。元王祯《农书》论瓜,“为种不一,而其用有二,供果为果瓜,供菜为菜瓜”,就其所说,甜瓜、西瓜是果用瓜,哈密瓜是甜瓜中的厚皮种类,也属果用。冬瓜、南瓜、丝瓜、越瓜、瓠瓜则是蔬用瓜,它们共同构成我国传统瓜业的主要品种。为了充分展现我国瓜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按出现和传播兴起的时间先后顺序,就这些品种的栽培起源、传播发展逐一进行梳理考述。值得注意的是,排在前面的五种,即瓜(甜瓜)、瓠(葫芦)、冬瓜、越瓜、哈密瓜(厚皮甜瓜),是我国文献记载原有的,我国应为次生乃至原生中心,后面的四种即黄瓜、西瓜、丝瓜、南瓜,是明确外来传入的。本土原产 一、甜瓜 甜瓜是种质资源最为丰富复杂的种类,今园艺品种有厚皮、薄皮之分。《礼记》说为天子削瓜,《北史》记载王罴为人俭啬,见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罴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曹丕所说“沉李浮瓜”,薄皮甜瓜肉质松脆,成熟时中有空腔,而能浮于水。《墨子》所谓“甘瓜苦蒂”。这些细节充分表明,我国上古、中古时期,人们一般泛称瓜均为薄皮甜瓜,后世泛称果用之瓜未指明品种者也都为这类薄皮甜瓜。 甜瓜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品种,《诗经》所说“七月食瓜”即是。相传尧舜时许由《箕山歌》有“甘瓜施兮叶绵蛮”,春秋《墨子》有“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汉魏古诗有“甘瓜抱苦蒂,美枣生刺棘”之语,时代未必完全可靠,但说明至迟到汉朝“甘瓜”之名开始出现。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西晋嵇含《瓜赋》将灵芝、芙蕖、甘瓜并称云芝、水芝、土芝,《齐民要术》所引《神异经》(传为汉东方朔所撰、晋张华注,后世多表怀疑)称椰子“华如甘瓜”,前者泛泛形容,后两者均明确指称,表明最迟晋宋时“甘瓜”这一名称已基本确立。至迟唐代,甜瓜的名称在孙思邈《千金要方》等本草医书中已频繁出现,所指即甘瓜,宋以来逐步取代甘瓜成为通名。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甜瓜之味甜于诸瓜,故独得甘甜之称”,是这一名称流行的原因。香瓜最初多作为甜瓜之一种,而后也渐有通名之势,所谓甘瓜、甜瓜、香瓜多数情况下都是异名同实。 我国有可能是薄皮甜瓜的一个原生中心,至少是次生中心,栽培和食用的历史极为悠久。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以出土蚕丝著称,同时也出土甜瓜种子,说明距今~年的先民们已经种植食用甜瓜。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甜瓜种子,尤其是出土女尸食道、肠胃中发现大量甜瓜子,湖北云梦、江陵、江苏邗江、广西贵县等西汉墓都出土甜瓜子。西汉后期的《氾胜之书》有“区种瓜法”,根据《齐民要术》的解说即属甜瓜内容。这些都表明至迟到汉代甜瓜的种植已有很大的发展,此后一直为我国各地最常见的栽培品种。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甜瓜品种极为丰富,清人吴其濬论述道:“甜瓜类最繁,有圆有长,有尖有匾。大或径尺,小或一捻。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或黄斑糁斑,或白路黄路。其瓤或白或红,其子或黄或赤或白或黑。要之味不岀乎甘、香而已。”先秦时《诗经》中有瓜、瓞之分,大瓜为瓜,小瓜为瓞,所说应主要是大小两种不同品种。汉魏以来,《广雅》《广志》、文人《瓜赋》及一些杂史杂记中出现不少各地奇瓜异名。而以瓜色青绿者最为正宗,晋人《广志》所列有乌瓜、春白瓜,应是指不同颜色,另狸头、女臂之类应主要说形状。但这些品种,唐以前都未见有进一步的记载,唐以后也多无明确的后续信息。 晚唐五代以来,出现一些新的品种信息,后世逐步落实为甜瓜的主要品类。如晚唐释贯休《秋居寄王相公》“山童舂菽粉,园叟送银瓜”,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徐氏《宫词百首》“沈香亭子傍池斜,夏日巡游歇翠华。帘畔玉盆盛净水,内人手里剖银瓜”,所说银瓜是指瓜中的白皮品种,后来成了固定的品种名称。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瓜青、白、黄等色,有名金皮、沙皮、密瓮、算筩、银瓜。”同时地方志中也有反映,浙江绍兴《(嘉泰)会稽志》:“越有银瓜、握青瓜、算筩瓜。握青谓其小,可藏握中;银以色名;筩以状名。”台州《(嘉定)赤城志》:“瓜有金瓜、银瓜等种,又有名八棱、约青、算筩者。”两地相近,有同有异,所谓握青、约青指大小仅一握,应即《诗经》所谓瓞之类。元人《(至顺)镇江志》“:甜瓜,种有大小,小而黄者曰金瓜,白者曰银瓜,碧者曰香瓜,又名一握青,其大而青,质斑纹者曰华瓜。”所说未必完全确切,但依瓜色分,青者称香瓜、甜瓜或青瓜,黄者称金瓜,白者称银瓜或白瓜,青而有斑纹者称花瓜,成了后来甜瓜品种的几大类型,除一些地方独有品种外,各地方志所载都大同小异,构成我国薄皮甜瓜品种的基本类型。 △《诗经》中描绘了先秦时代古人在田梗上种甜瓜的场景:“中田有庐,疆场有瓜。” 甜瓜分布极为广泛,我国但凡有瓜的地方都少不了甜瓜,即在哈密瓜盛行的新疆,仍有方志记载哈密瓜的同时记载普通甜瓜。甜瓜适应性强,种植简单,生长期短,北朝《齐民要术》称“瓜收亩万钱”,元王祯《农书》称甜瓜“一枚可以济人之饥渴,五亩可以足家之衣食”,可见经济效益比较突出。因而在我国各地,无论小户零散自种自给,还是大小规模种植为业都极为方便而普遍。而品味既甜且香,瓜肉或脆或酥,食用价值较为显著,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二、瓠(葫芦) 瓠,上古、中古时期人们多与“瓜”相提并称,为瓠类植物的总称,至少包括一种名匏的植物。《说文解字》解释瓠、匏二字互训,《诗经》的早期训解也多将两字视为同义。但就《诗经》相关的内容,无论就字形还是语意看,都是明显两种不同植物。《小雅·南有嘉鱼》“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小雅·瓠叶》“幡幡瓠叶,采之亨(烹)之”,果实与叶味甘,可用作蔬菜,这是一种。《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的壶,通常多视为蔬用,也即此种。《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所说是可以渡水系身作浮标的葫芦,《大雅·公刘》“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是以匏酌饮,都是制作器具使用,这又是一种。两种多以瓠、匏分别称之,后世所谓“甘瓠苦匏”即是。从文字使用上说,瓠既是类名,可以概指包括匏在内的同类植物,又是其中可以蔬用的独立一种,后世多称瓠瓜、瓠子。匏则是瓠中一种,魏晋以来多称作葫芦,嫩时也能食,只是稍苦些。 瓠类作物的利用历史极其悠久。瓠或葫芦子,在我国新石器以来的出土文物中屡屡有见。大约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新石器遗址即发现有壶芦皮,距今~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小葫芦种子和瓠皮,另如杭州北郊半山水田畈新石器遗址曾报道的西瓜籽,被重新鉴定为葫芦或瓠瓜籽。《诗经》多篇言瓠匏,《论语》《庄子》都有以瓠匏譬喻说理的著名说法,《齐民要术》将“种瓜”“种瓠”与黍稷、粱秫、大豆、大小麦、水稻等相提并论,都充分反映瓠类作物在我国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宋以来地方志渐起,瓠与匏、瓠子与葫芦是各地方志物产蔬果中最常见的品种。我们举几例作为代表,如福建,明《(弘治)八闽通志》:“瓠,似越瓜,长者尺余,夏熟味甘。又一种名瓠,夏末始实,秋中方熟,经霜可取为器,俗呼葫芦。”河北,明《(嘉靖)清苑县志》:“瓠,味甘,间有苦者。又一种名匏,所谓瓜匏之瓠,即今胡卢。”四川,清《(乾隆)射洪县志》:“瓠,瓠之甘者长而瘦,名曰瓠。匏,短颈大腹曰匏。”甘肃,《(道光)镇原县志》:“瓠子……瓠一名瓠瓜,皆甘滑可食,邑人晒干用者名瓠条。”“壶卢……有二种,有柄而圆者名甜壶卢,可为茹,经霜作瓢。腰细者名苦壶卢,又名药壶卢,入药用。”上述内容分属东南、华北、西南、西北四大不同地区,明清几个不同时代,所载有详有略,但都明确有瓠、匏两种,而匏者(葫芦)可蔬食,也可作器,典型反映了我国各地分布和使用的情况。由于瓠、匏嫩时均可作蔬,可烹可齑,尤其是匏或葫芦多制作勺器和盛放一些细杂东西的容器,在人们生活中多不可缺,加以瓜与籽的药用价值比较显著,自古即受到人们重视,也便演生出浓厚复杂的文化,专题研究者颇多。各地种植极为普遍,汉人《氾胜之书》就较为具体地计算过种瓠优厚的经济效益,直到清朝仍有方志记载有“种瓠为业”的现象。 三、冬瓜 我国冬瓜种植与食用的历史十分悠久。无论考古还是文献资料,都表明至迟秦汉时冬瓜已经受到人们重视。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早期墓、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原发掘报告所说西瓜种子后被学者确认为冬瓜种子,类似的情况或者仍有。这表明至迟西汉早期,冬瓜已受到人们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yl/4809.html
- 上一篇文章: 雅轩文化问候香瓜的功效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