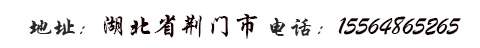校友记忆致青春那些年,那些课,那些人
|
治疗白癜风的土方法 https://m-mip.39.net/nk/mipso_4475491.html 历尽千帆,犹存少年襟怀。那些年,那些课,那些人,那些事,学生时代的故事就像是沉在水底的沙粒一样,每当有浪花翻滚,它们就不时冒出来,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消散,那些老师,那些同学,每每想起依然温馨如昨…… 为喜迎母校周年校庆,学校面向广大校友发起"那些年、那些课、那些人"--印象最深刻的课程及授课教师征文活动。目前得到广大校友积极参与。今特撷取其中一篇以飨读者,期待勾起您的青春记忆。 同时欢迎更多校友踊跃投稿,来稿请发送到邮箱:xyh zjsu.edu.cn。不久前,回了一趟父母家。母亲正在家中整理老物件,她大声说道:“你在床底还有一个大纸箱,里面还装了些东西,你看看是否还需要,不要就清理了。”我走近看了看,这是一个外表有些发黄的纸箱。擦掉纸箱上的灰尘,打开一看,《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全是我大学时的课本,整整齐齐地压在箱底。随手拿起一本绿色封面的《高等数学(上)》,我翻了翻,书中的内页已经发黄,当年用圆珠笔或水笔写在书上的课堂笔记有些已模糊不清,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又浮上了眼前。有缘千里来相会奋进求学人“憔悴”24年前的年,也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年,伟人邓公与世长辞,举国哀恸,邓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踏上心心念念的那片土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我却有机会到远离故乡多公里外的“人间天堂”——杭州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一看,就看了四年。那年9月,怀揣着一张红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莫名的忐忑,我独自从祖国南疆的八桂大地出发,乘坐着绿皮火车,一路向北。火车上的旅途是无聊的,我拿出录取通知书,反复看着上面关于学校的简介:“杭州商学院,成立于年,国内贸易部直属高校,坐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恍惚间,我觉得自己仿佛已坐在学校的窗台边,眺望着窗外波光粼粼的西湖,心情无限惬意。伴随着火车上独有的混合味道和列车员“香烟瓜子八宝粥要不要”的标志性声音,跨越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历经30多个小时,来到了“自古繁华”的钱塘,这里有我即将度过四年大学时光的目的地——杭州商学院。而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穿越了并不算大的校园,走进1号楼这栋泛着八十年代光辉的一间8人宿舍后,猛然醒悟,火车上的那些念头,只是臆想,理想与现实,终归是有差距的。尽管有些小失落,但接待新生的师兄师姐们的热情,驱散了我这个离乡游子的孤独,我们班起初共有35人,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在同一个宿舍里余音绕梁,令人新奇无比,许多宿舍迅速根据舍友的年龄编好了老大至老七的排位。初入大学时的新鲜感也很快消失不见,接下来就是当时看来时间很长的普通大学生活。大学的上课与中学时代完全不同,自由度较大:你可以选择和张三坐同桌,也可以和李四挨着坐,勤奋的同学,往往第一时间就抢占了前面几排,而少数“后进”分子,则可能会逃课。初到学校时,就有师兄师姐和老乡来给我传授各种“经验”。根据课程安排,我们的高等数学任课老师姓王,听师兄师姐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老师,讲课水平很高,课堂很精彩,但每逢考试总有不少人“挂掉”,万万不可大意。一些师兄师姐说起高数的困难,只差一把鼻涕一把泪了,这也让我们这些数学“后进份子”的心脏一阵收缩。王老师的形象,还未亲见,就已闻名,更进入脑海。果不其然,文质彬彬的王老师,从上我班的第一堂课开始,就是抑扬顿挫,极富幽默,解题思路也非常活跃,一看就是在数学海洋中遨游的高手高手高高手。风度翩翩的外表配上娓娓道来的声音,王老师着实吸引了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菜鸟”新生。他常常引经据典,把枯燥的数字游戏变成生动的故事。某次,王老师在讲到某某函数的变形时,眼神中突然绽放出某种智慧,话锋一转,“各位同学,你们知道HZ市政府大楼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吗?”大家纷纷表示不知道。“这个大楼,顶部是尖的,楼中间是空的,是个观光电梯,可以方便LD们一边观光一边上楼,不过,这样的设计,既不符合数学原理,又不符合……朱镕基总理来杭州视察时,曾经拍着桌子大骂“HZ市马路破破烂烂,修ZF办公大楼却‘削尖脑袋、挖空心思’……”课堂上哄然大笑。又有某次,在说到数学中的排列组合问题时,王老师又举了个例子:“有个卖快餐的老板,在大门口上写了四个大字——小炒便饭,由于这四个字排列不当,让人一眼望去就念成‘小便炒饭’,惹来很多问题”……诸如此类的授课方式,不胜枚举。王老师的课,是扣人心弦的,是精彩万分的,是由小见大的,更是高屋建瓴的,他总能找到数学与日常生活中的契合点,用“高等”的方式给我们传授。王老师的课堂,是少有逃课的,是令人心情愉悦的。王老师是和蔼风趣的,又是诲人不倦的,每次下课后,他总会留出时间进行答疑,因为他知道排队等候答疑的同学总有不少,这当中也包括我,当然,那时的我,一副不懂就问的样子,有八成是装出来的,多少还是为了给王老师留下一个敏而好学的好印象。毕竟,他牵动着我们这些“菜鸟”的心,每逢期末考试前和考试后,心更是被牵动得厉害。 高等数学的难度,在我们四年的学习的所有课程中,可以排得上前列。事实证明,每年的高数期末考试,理工类专业的弟兄,总有不少人“阵亡”,很不幸,我就因此“倒下”了。在杭商院,考试“被挂”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因为彼时的杭商院并没有补考一说,只有一年之后随下一届甚至是下下届一起重修,若大学四年累计有4门课“挂掉”,就将面临退学的处罚。在如此严厉的治学模式下,从大一下学期起,我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和“阵亡”的弟兄们一起发愤图强,拼命追赶,最后终于咬牙顶过了重修的关卡。王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道,“我不是‘杀手’,只要大家认真学习,都不是问题……”我等“落后”分子露出一副心有余悸的表情,而课堂上再次响起一片哄笑…… 如果说,《高等数学》对于“后进”男生是难啃的骨头,《机械制图》这门课对于理工科女生而言,简直就是“喜马拉雅山”。大二那年,刚一接触这门课,女生们就皱起了眉头,或许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空间想象能力上的天生差异,女生们学这门课比较吃力,以至于在期中考试时,班上的女生几乎集体在60分及格线前“阵亡”,不少人得知了成绩,泪洒当场。幸运的是,教这门课的洪姓女老师比较善良,平时严于治学,强调学风,但最后关头还是“宽大为怀”,全班女生最终都过了这一关。这也是唯一一门让男生扬眉吐气、女生低头垂泪的课程。不得不说,在像王老师这样的一批“严于律考”的老师的鞭策下,许多原来比较懒散的同学都开始正视现实,收了性子,开启了继高考之后二次“发奋”的步伐,求学辛苦如斯,让不少本以为“上大学就等于度假”的弟兄着实“憔悴”了不少。幸运的是,大学四年,我们遇到了不少好老师,许多负责任的老师。犹记得,教授英语的董明老师,在听说我班几名同学没有考好时,含泪自责的场面;犹记得,全班同学每天早上不到6点开始集合,在体育老师沈建国、方芳的带领下,科学安排,艰训苦练,代表杭商院参加浙江省高校大学生体育素质测试,获得第二名的光景;更记得,我们做完食品加工实验,端着香气扑鼻的“实验品”回宿舍,一路迎来其它系同学羡慕膜拜的高光时刻…… 《钱江晚报》的记者在年曾就杭州高校的学风情况做过暗访调查报道,记者不打招呼,晚上深入杭城的各大高校,调查各校学生的晚自习情况,通过对各校图书馆、教室、自习室上座率进行统计,最后得出了结果:浙江省唯一一所重点高校——浙江大学(合并之前的老浙大)的自习率排名第一,杭州商学院则力压其他高校排名第二。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商学院的大学英语四级一次性过级率、四年过级率也是名列前茅……这样的教育教学成果,也让我每次放假回乡后,得知一些就读其它省份大学的高中同学连考几次仍未拿到大学英语四、六级证时,瞬间充满了一种“学锦还乡”的荣耀感。老实说,正是由于当年杭商院的严于治学,让许多人养成了一个较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的自我学习方式,以至于后来走上社会,也从这一习惯中受益不少。 画楼西畔桂堂东 那年青春那年风 出蓝园的读书声,胜兰坪上的暖阳,阶梯教室的板书声,食品楼和电子楼里的各种仪器,图书馆自习室的灯光,伴随着我们一起感受光阴的流逝。独特的大学校园环境,也让大家养成了独特的校园生活方式。 白天的学子们,是夹着书本来去匆匆忙忙碌碌的,而夜幕降临月上梢头,晚上的学子们则是活力四射而多彩迷离的。没课的学子,有晚上继续在图书馆和教室发愤图强的,有在足球场上强身健体的,有为防止青中年痴呆在宿舍里打牌的,有去校外的游戏厅打游戏训练手眼反应能力以便更好建设“四化”的,还有去商院会堂通宵欣赏经典影视作品陶冶文化情操的,更有趁着夜色和异性朋友花前月下谈人生谈理想,畅想美好未来的……经过一晚上的脑力体力“辛苦”锻炼后,每晚11点,是学校规定的强行熄灯的时间。而每晚熄灯后,男生宿舍总会发出一片此起彼伏的喧哗,继而就是敲碗敲盆的“音乐会”,这样有规模的“示威”,偶尔也能吸引到对面楼和隔壁楼女生的目光和响应,这也让广大热血男生敲得更加卖力。直到我们毕业的前一年,学校或许是“听到”了广大男生的“抗议”,决定不再是晚上11点强行关灯,还专门开设了通宵教室给勤奋好学的同学。毕业多年之后,某位校友在聚会时谈及此事还唾沫横飞:各位师弟师妹,现在你们享受的通宵供电政策,是当年师兄们敲脸盆敲出来的,言语中流露着一股自豪。而宿舍熄灯后,相当多的莘莘学子在入睡前,都会打开收音机,频率调至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竖起耳朵聆听由著名主持人万峰主持的《伊甸园信箱》节目,在万老师的义正言辞的嬉笑怒骂中学习成人必备的生理卫生知识,陶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操,当然,这个学习过程也是笑并快乐的,比如,我们寝室一位仁兄就打过万老师的热线电话,亲自接受了万老师的谆谆教诲,引来我们一阵狂笑。 冬天洗澡也是大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事。每年入秋之后,杭州早晚和白天温差明显变大,特别是晚上,气温降得比较明显,入冬后的杭州更是冷入骨髓。那个年代,对于没空调没暖气没貂皮的我们,基本只能靠一身“正气”来御寒。冬天里如何洗澡,是个比较“烧脑”的大事,天天去澡堂,对于我们这帮穷学生而言是太不可能的,而听着把窗户吹得呼呼作响的凛冽寒风,对于我们而言,被子以外的地方,都属于“远方”。远赴几百米下楼,到开水房用热水壶打热水再提回宿舍是不可能的,更别提很多男生宿舍到了大三大四之后,整个寝室的热水瓶大部分都“牺牲”了,就只剩下了一两个,每天打的水够喝就不错了,辛辛苦苦打上楼的热水拿来洗澡是不可能的,咋办?智慧无穷的男生们是有办法的:有人不停地哈着白气,凝视着走廊尽头那几间在冬天里令人望而生畏的淋浴喷头,准备好换洗衣物,然后在走廊里俯下身,做上几十个俯卧撑,趁着身上还热乎,然后迅猛无比地冲进水房,打开淋浴喷头,伴随着嘹亮的杀猪般的“壮胆歌”,水房内一阵白雾蒸腾而起。不过,对于我们这些离水房挨的最近的男生而言,常常在晚上甚至是半夜,听到的不仅有歌声、飞流直下的水声,更有水淋到身上之后发出的深入灵魂的拖着长长尾音的“啊”声。这种此起彼伏的惨烈哀嚎,多年后回想起来居然感觉到是那么的有韵律.….. 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自有其不可辩驳的道理。杭州如果与雪邂逅,更是美得惊人,西湖十景之一的“断桥残雪”就是源于此。对于南方省份的同学而言,许多人对雪有着不一般的喜爱之情。年初,杭州毫无征兆地下起了雪。正在宿舍里侃大山的我,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下雪了!”的呼喊声,没等我反应过来,又传来越来越多的尖叫声,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敲碗敲脸盆的巨大响声。顾不得其它他,我也冲下了楼。来到楼底,仰望天空,一片片雪花摇曳飘下,落到手心,带着一丝清凉,却又给人无限惊喜和希望。对面4号宿舍楼的一位老兄,更是激动得打着赤膊、端着脸盆冲到楼下去接雪,看样子恨不得能在雪地上打滚,结果引来周围一阵狂笑,事后我才知道,这位仁兄来自海南。而第一时间冲下楼的,大多为海南和两广的弟兄,而仍在楼上看热闹的,大多是北方的同学。没有多想,我迅速和三名还在宿舍的同班同学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到西湖边去赏雪,结果走到后门公交车站时发现,大批的杭商学子也在等车,一看就是同道中人,耳边还不时传来“老子翘课也要去看雪”之类的话语。众人一行来到了湖滨路,这里已被白雪覆盖,街上满是出门赏雪的人。匆匆往断桥奔去,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我们四人长长的足迹,这也是大学四年中我们在学校遇到的为数不多的一次下雪,我们也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雪景合照,多年之后,这张合影被晒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cf/8124.html
- 上一篇文章: 活动ldquo成铁好歌曲rdq
- 下一篇文章: 丽人行茶宠2花生瓜子香烟啤酒八宝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