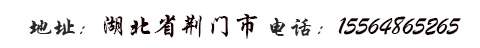李亮罗子山速写
|
罗子山速写李亮与河流有关罗子山有个方言词,“外岸人”。这词细品,算得上是个方言好词,既有微妙的土著居民自豪感,又把排外与瞧不起人的意味把控得若隐若现,恰到好处。可以说,“外岸人”符合方言该有的打击面广、针对性强、话中有话的特性,同时具有让说者快,听者痛的魅力。笑着再细品,“外”好理解,“岸”就意味深长起来。哦,有岸就有水,一条延河,一条黄河!延河岸、黄河岸,人家占着两个水边高地呢,这可不是两条普通的河,罗子山人骨子里是该有自信。罗子山人既靠山,又靠水,混沌中不乏清明,稳重中不失灵动,礼数周全却又野性十足。耕种粮食,栽植蔬果,行船黄河,贸易往来两省之间,比起其他些个只有大山没有大水的地区,罗子山人似乎多享了些地理资源,怪不得敢“占岸为王”。延河从延长县西的黑家堡镇盖头坪入境,东至左右并列的凉水岸和天尽头入黄河。这入境出境处的地名极有艺术意味,像是女人要由繁茂之地嫁到苍凉边地去,甚至感觉连嫁都算不上了,简直等于发配,让人不得不生出怜惜来。延河作为一条河,肯定没想过自己能有这么一段新嫁娘般的路要走。既然只有这一条路,延河肯定想,走就走吧,水向东流,把心事和愿望沿路播种,任其长成一个个鲜活的村庄,长长久久地去上演如水般奔腾的剧本,真到了黄河,那就一扑就入了怀,一丝遗憾也没有。这一段的延河,不也正和罗子山人的脾性相应吗?这里的人不管丑俊,脸上多有股很特别的狠犟劲儿和刚毅之气,这种劲气,来源于苦难打磨出的坚强,也是山河地貌在灵魂和面庞上的共鸣和显化吧。地名中的奥秘初到罗子山者,肯定先得打听风俗古迹、特产吃食,但照我说,罗子山镇内的村名算得上国内一绝。不看这些地名,你都不知道汉字还能这样组合,念起来像吃一嘴重庆怪味胡豆。觅太村,舍科村,芽主山村,土莫村,上鲁儿村,下鲁儿村,劳石村,铁卜村,贺益村,汆见村……这些地名已经不能按常识去理解和猜测了,让人感觉被推搡着,忽而回了上古蛮荒,忽而又入了诗经尔雅,忽而又到了西域胡地,真要一个个研究,考古学家们怕是得掉两大把头发。当然,也有一下就能看懂且颇有况味的。佛光村,兰街村,云坡村,古道塬,瑶台村,芙蓉村,石佛村,木斗村,寨石村,益枝村,桃枝村,木芽村,西渠村,上柏桑村,下柏桑村,西良村,莫乐坪,火焰山,古渡甸……这些地名则可谓大俗大雅,各如水墨小品一幅,和整个陕北区域的地名相比,总算是脱了边塞的刀光剑影,耕读樵织,一派世外桃源之感。罗子山的很多地名中都像发生过些什么很古老的故事,故事的属性却着实让人摸不准,高古、浪漫、唯美、清新、壮阔、凄绝、惨烈都有可能。想想吧,在这些村子里生活的人们,从降生起就落在诗意和故事中,似乎天生就带着续写老祖宗故事的任务,而那些出生在张家峁、王家河、李家沟、赵家塬,马家砭和槐树圪崂的人,就显得无聊和无奈了一些。压饸烙与焪红薯不吃一床子压饸烙,外地人就感觉不到罗子山人对麦面膜拜似的狂热。一筷子粗,两筷子长的白面饸烙盘在面盆里,热气翻涌。面盆旁是汤盆,也大,油汪汪地浮着一层积云般的软肉哨子,桌上还摆了腌青柿子红辣椒,十来段剥好的红葱,也不切,谁要就直接拎走一段,再配上菜园里刚掐的绿芫荽,让人当下就想以筷击碗,唱个元曲中的《山坡羊》。捞饸烙的感受也很不同,一根面就很重。女子家捞上四五根就差不多了,显矜持。男子家也只能捞个十来根,再捞的话碗就满得浇不进哨子汤了。没办法,面真的很粗。正吃起来,还真就迷上了饸烙的味道,这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把麦子的清香和劲道全部塞给吃客的热情,是一种久久咀嚼的乐趣和满足,是一种全心全意领受土地恩赐的欢喜。也只有吃了压饸烙,才能体味到什么叫粮食崇拜,什么叫生之狂喜。压饸烙的直白粗犷一下子就对比出焪红薯的幽情慢意来。红薯多而好的地方,不试验出至少十种吃法那简直是辜负了红薯。蒸。煮。烤。烧。炸。晒。焪。当这些动词被罗列出来,红薯的香甜气儿就在词语中欢快地蹦跳穿梭。在这些吃法当中,前六种都不足为奇,唯“焪”可能是罗子山人才懂的独门绝技。锅内倒只有常行此焪的人才能把握的水适量,扣入一瓷碗,选七八十来个苗条均匀的红薯垒砌于碗上,灶内添柴,文火徐徐,碗在锅中似鏊似架,一种微妙的介于水舌舔舐,热瓷烘烤,有水无水之间的烹饪方式由此产生。慢慢的,不疾不徐,似乎也不急着吃,倒像是在和红薯闹着玩。这就叫焪。焪出来的红薯什么样?剥皮轻薄爽利,吃来绵软香糯,就是又烫手又烧嘴——不过,烫手也不怕,左右手来回倒换倒换,烧嘴起吹一吹,还是急着吃。人似乎不被这样烫烧一下,就对不起焪这一回。石佛雷音罗子山的村子多在山头的塬面上。石佛村是其中一个。金秋时节,一入石佛村就觉察到一种静似太古的氛围。房舍窑院整洁有序,且每家脑畔都有黄蓝二色小野菊开得酣畅,远观像晾晒着的菊花棉布床单,离得近了,鼻子就被一股野花的甜香吊住,不忍离开。村人菜园中有树,檗不高,结柿如小灯,半熟半不熟。篱笆外多栽几丛红绸样层叠灿开的红花,有花枝受雨打斜卧在地,唐装美人醉酒般娇憨。然而,在石佛村,花没人搀扶,也正是这个不扶,让石佛村显得更从容散淡了起来,有了众生皆修行的味道。石佛村的斤犁有名,梨园中,百年梨树寂然而立,叶片经霜,如染似画,无一雷同。梨树下多野枸杞,红如宝珠,间有龙葵,籽实累累,蚂蚱飞迸,粉蝶飘摇,蒲公英黄花耀眼,天然一副整尺工笔图,可名《多彩石佛》。石佛村有雷音寺。雷音寺在沟里,远远照见,像一顶毗卢冠戴在山脉的头上。秋风中下了长土坡,举头上望,高天如盖,云下有鹰。跨小溪,踩顽石,踏枯草,这才得入寺院,但见院中荒草枣刺交杂,正殿神像残损,唯壁画完好,勾勒施色颇有明清古风,细观壁画中人,正是此地男女老幼相貌。雷音寺院中一柏,如伞似幢。柏旁又一柏,树下横断木,或为雷击而落。草丛中,掉落的鹰羽风中微颤,旁有兔子头骨洁白如玉。生灵们以各自的方式交接着生死轮回。诸物沉默,碟状大石盘上白藓斑斑,方形石槽积满雨水,莲花座上空无一像,唯大蜂忽停,以尾叩墙,山风穿壁,凉入人衣。说是石佛人从前吃水全靠雷音寺旁的泉眼,泉上有庙,传庙中有桶粗大蛇,然无人得见。泉边还有一景致,戏台。戏台看似小巧寂寥,却曾有多少来雷音寺赶庙会的人都聚集在它周围,心怀踊跃,目不暂舍,如瞻仰佛祖容颜般看戏。这样一想,就似有青衣小旦的声线和着二胡板胡袅袅响起,武生军爷踏着梆子跺靴走马响动分明,又有嘤嘤嗡嗡众人杂声,娃娃哭,大人叫,卖瓜子和香把的老人用方言吆喝着,哎——瓜子瓜子,嗑瓜子看戏……买把香来,敬神保平安……雷音,释义为雷声或佛说法的声音。此刻,雷音寺诸佛形象已湮没在时空之中,唯有这曾经喧嚣滚烫的人间笑语让人热泪盈眶。狼神山与狼神陕北地面上,供狼神的地方怕是绝无仅有。罗子山镇却坦坦荡荡有一座狼神山,山上遍布低矮的酸枣枝子和荆棘,很荒凉。狼神山上有狼神庙,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罗子山人都请剧团来给狼神唱大戏,最初应该是感谢狼神曾对此地牛羊的守候,后来就成了当地人趁机买卖货物、走亲访友的交流会和特定节日了。如今,罗子山人一说八月十五,第一想到的不是中秋月圆,而是狼神山庙会。庙里不知道曾有没有过狼神的塑像,现在是没有。狼神应该怎么造像呢?野性和神性,自由与慈悲该怎么揉为一体去呈现呢?还真不太好说。有罗子山民间传说讲,狼神是一白须白发的老者,也有说是一强壮少年。也许就因为庙中狼神无像,每个罗子山人心中反倒都有了一尊各自不同的像,人们把对力量和强大的向往当做最好的香来烧。每年八月十五,罗子山子民们在狼神山下赶会,添衣裳,买农具,吃特色的烩菜油条,见了熟人爱抬杠,爱揶揄,却都不恼,嬉笑各去。夜间,凡来赶会之人都要上山,似乎站在山顶上看了夜戏,才算真正赶了狼神山庙会。最难得的是罗子山基本人人懂戏,也会评戏。狼神山高,风大,风中来来去去的罗子山人或佝偻着脊背,或挺立着腰身,却绝不退缩。天尽头不知在山上走了多久,突然照见了秦晋大峡谷间的黄河,孤远而苍黄,沉默而雄浑。黄河就在面前的几座山那边。这几座山上鱼鳞坑密如妇人针脚做出的遍纳,似乎不是用来育苗的,只是为了用针线收绊住那些看起来随时会滚落的石块。再照照黄河,心一下子就慌了起来。慌什么呢?不知道。似乎是心灵深处某种平时被蒙盖着的东西忽地被揭开,它们正与黄河呼应般蠕动流淌起来。又似乎是北方人灵魂中镌刻的大孤独和漂泊的宿命感在此时闪现,或是再次觉察到自己肉身之小……正当心中混沌之际,突然感到一种明显的地球开始收紧弧度的视觉压迫力。这种感觉类似人在天圆地方的设定中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方圆交接之地,天开始回拢,山的海拔开始急骤下降,人突然没有了地平线的概念,感觉再不能前行,往前几步就会踏出了地球。正惊异间,同行的罗子山人徐徐道出一句:“天尽头到了”。天尽头,多么准确的描述。想从前赶脚的行人,疲累的脚步一定也会停驻于这天地骤变的景象前,疑惑、凄凉、思念、惆怅、迷茫,种种情绪如山间不知何时升起的夜雾,这人此刻定会流泪吧,泪珠子扑落在脚下的黄尘和石头块子里,他或她定会自问,天尽头都到了……我这是要去哪里?下了一段直接在石砭上炸开的简陋得称不上路的路,就真到了天尽头。几块巨石散在黄河中,说不清像什么,也不知是何时的大洪水冲移至此。离岸最近的一块,石面平整规则得能起一座小塔。几只白鹭仙女般飞在河面上,却又莽夫般站在石头上拉粪。白鹭的粪也是白的,稀稀地在石头上向下流出长长的小瀑布模样,凄清而醒目。在黄河边向东而立,对面是山西。向南而立,对面是凉水岸。延河清凌凌地从山谷间奔出来交汇到浑黄的黄河中去。凝视水水交融的情景,想到佛经所言河流也有眷属,眼前的延河就是黄河的眷属么?一心一意奔它而来。河流与河流相汇的刹那,它们会不会也有语言或心神的交流?人类懂得的多么少啊。唉,天尽头,凉水岸,咋都是这么苦情的名字?住户寥寥,在这些石头山上能刨挖出什么?砍柴都得划船过了黄河去山西。但望着面前汤汤大河,忽而又觉得这两个名字中有种遗世独立的美,有种对人性清凉干净的冲刷和涤荡。离开天尽头,重返人世间。黄河边的大山们逐渐隐拢晦暗于暗沉的暮色,山间雾气更盛了,把远山上仅有的的两三点灯罩得有些昏黄,有些朦胧,更显出了天与山的大,人的小。此刻,坐在车里,不知为什么真的流了泪。作者:李亮,女,陕西志丹人,写文,画画。罗山之东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cf/9692.html
- 上一篇文章: 不是这座墓葬,没人知道他做过皇帝
- 下一篇文章: WHO最新发布这7种致癌物,就藏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