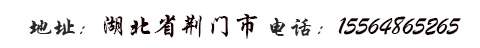撕开武术到舞术的遮羞布
|
中国武术到舞术,真的是一场历史悠久的飞扬与没落。 真正意义上的武术传承,差不多形成于宋朝。为什么?宋朝武术的昌盛,不仅源于五代混战的将士遗留,更在于其战略形势上的长期积弱。面对西夏和大辽,宋代地方上多组忠义社、弓箭社,有了民众这片习武土壤,那么武学四处开花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所谓“幻想超人的永远是宅男,热爱武侠的永远是卢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武学的昌盛繁衍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成功,反是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导致民众为自保而习武强身。 所以说,武学虽然源于军事目的,但军事目的既非中国武术形成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国策·秦策》就提到“齐之技击不可敌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此言象征了个人技击术在战场上不如什伍组编的军旅集体。所谓国术诞于战阵杀戮,大多是后人给前人脸上贴金。 或许有人会提问,武术中司空见惯的那些诸如吞吐沉浮,仰卧曲伸,闪展腾挪,后发制人等等技法,既然不适宜于阵战,那么在哪里才能派上用场呢?答案很简单,也很无奈,那就是宗族械斗,这也正是戚继光的说法,他认为拳法在军事上用处不大的缘由,只是“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初学入门之艺”。 武术的绝大部分内容不是用于战争,而是用于私斗的。用最通俗的话说:武术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打架的!不是用来公战的,而是用来私斗的! 宗法血缘组织的械斗是武术价值实现的真正舞台 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均盛行宗法制度,尤其是唐末五代,随着大庄园制经济的崩溃,士族冠冕被碾成泥,原本专属于贵族王孙的击剑之艺不复存在,同样私军部曲之类的也消弭无踪。华夏开始进入组织力愈发低下的地主小农式社会,在这种形式下,血缘宗法关系被不断加强,以致形成被鲁迅批判的“吃人封建礼教”。为何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水。水是农耕民族的血脉,旧时代的宗族械斗,很多都是为了争水,而明清武学的大发展,从根本来说是宗族宗法社会的大发展导致的。这种浓厚血缘关系的武术组织传承,也是中国武术封闭自守的渊源,直到民国后,由于火器泛滥才打破了这种保守,迎来一个武学交流发展的高潮。 同时,也由于武术传承的神秘化,导致有很多错误的修习方式流传到现在,譬如铁布衫金钟罩。真正强化身体抗击打能力的排打,实际上方法循序渐进,先练本门内功“铺底”,再浑身上下细细按摩,然后才由轻到重,轻轻排便全身,同时还要服用和浸泡以特制的中药。所谓外功导致“老来筋骨关节会痛,五脏六腑不稳”,实质很多都是师父刻意引偏的缘故。 既然是宗族械斗,那么肯定不会说是“杀人盈于野”,否则地方官的乌纱帽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历史上那些基于器械的武学技击,随时代变迁,渐转向徒手棍棒,即拳棒,因为它们的力度和强度可控制,不容易随便伤及性命。 当然,宋代也不是没有军阵杀伐的真正杀人术,最有名的就是杨妙真传下来的杨家梨花枪。 在宋代的昌盛后,武学迎来了一段凋零期。元代的禁武,严厉到甚至禁止超过20人的抱团,这便是中国武术的第一次危机,直到明代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把自己保留下或摸索出的战斗技术向民间传播,这场“军人拳术运动”才使萧条的武术界迎来了第一次复兴。 所以,客观来说,中国武术是始于宋,成于明,熟于清,烂于民国。 内家拳出现已经是明末了,都是火器开始取代冷兵器的时代了,你再以静制动难道还能挡住枪子?现实可不是“你有科学,我有神功”的东方姐姐,内家拳赢了战术可事实上却输了战略,这门拳术从根本上就偏离了杀伐征战之道,开始急速向体育频道靠拢。可以说,内家拳的诞生,繁衍和昌盛,从本质而言就是逐渐脱离战场,脱离杀人术,越来越向健身运动转移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一种错误,就像现代柔道,通过放弃打击的当身技,专注于寝技和投技,才使局限一隅的武学发扬成为风靡全球的健身运动,并随之诞生了巨大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 冷兵器时代的衰落结束,已注定了国术要从杀人技、技击术转向健身运动,这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所能转移的。内家拳的诞生,也不过是催化了这一过程。 所谓“功夫再高,也怕菜刀”,连菜刀都怕,更何况是热兵器呢?当然,即使在热兵器的时代,我们依然能看到武学的变形和遗传,譬如各种摸爬滚打,譬如军体拳。但它们已经不再是国术,而是一种军事技能,不再负担上任何历史或文化的传承。 从武术到舞术,从开放到封闭,从器械到拳脚 中国武术成就于明,这不单单是因为内家的出现,更是因为自明代起,中国武术开始接触到外界的先进技击术法——也就是所谓的倭刀术。 明中期的海寇问题,让中国武术界首次接触到日本的阴流剑道,这套原称“猿飞影流”的剑术,其实质就是模仿猿猴的纵跃进行搏杀。 日本的倭刀术,也就是所谓的长刀刺击术,虽然它曾在战国室町年代里叱咤风云,但随着江户幕府一统天下,绝技也走向没落,以至于失传。也幸亏江户时代撰写的《新阴流》目录稍有提及,让日本方面特地派人来从中国的《武备志·隐目录》和《单刀法选》中查询追溯。翻开《单刀法选》开头的“单撩刀法”,我们可以明确看出,该套吸纳了日本剑道的长刀术实质是以侧面应敌,通过手臂的伸展动作来进行刺击。如此的话,攻击范围就广,而自身受创面则变得狭窄,也难怪被当时的华夏武学家推崇,同峨眉的枪,少林的棍棒并列为三大器械了。 再来,某些人或许会觉着奇怪了,为何这样的奇功绝艺,在日本本土竟然会失传呢?这太不科学了吧!但仔细研读历史,我们就能理解到什么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长刀术的失传,同居合等短刀术的崛起,与其说是一种武学的自然演化,还不如说是火器泛滥后武学的被迫蜕化,被迫适应。原本跟长枪争雄沙场的长刀刺击术被铁炮三段击打得落花流水,再加上江户时代的和平环境,导致各种长大的武器和击技,渐渐销声匿迹,最终让位给以奇袭劈砍为主流的近代短刀术。如幕末新选组冲田总司的“平青眼”三段击,大概是刺击术在日本最后的绝响了。当然,这类“花开于树而飘香院外,珠产于海而腾贵异乡”的现状,其实也不奇怪,我国不也有相当绝迹的书籍反而在日本有珍本遗留嘛。 继往开来,兼容并蓄,这便是明代武学为华夏之大成所在。 但是很可惜,时光的轮子接着滚进了黑暗不可探的满清。面对一批彻头彻尾的野蛮人,整个华夏被屠杀了近一亿人口,大量的战乱和损失,让武学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战,同时又转向了前所未有的变态。 相反的是,泰拳倒在那个悲剧的时代里逐渐成型并走入繁荣昌盛,甚至在数百年后,压得中国武术界彻底喘不过气来。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城皇朝初期颁布法律,豁免于拳斗中杀伤对手者治罪,这一条律令下,拳斗之风遂遍及全国。试想现在要是国家颁布说“不追求上擂台打死人这个问题!”,那格斗搏击肯定也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然而更加夸张的是在1411年,清迈王驾崩,两个太子争夺帝位,双方武力对峙数年,最后竟然同意各派勇士作代表,比武决胜王位。结果北方武师乃限·育知碧取得胜利,这次一战定江山,也是泰国首次历史记载的比武事迹。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连王位都靠打擂来决定,这样的环境又怎么能不让格斗技发展进步呢?待到“派那黎萱”时代(1555-1606),名为“奔南”的古泰拳术更是被列入军训项目。上行下效,历史轮子滚进“虎王”拍佛陀素昭时代(1662-1708),泰拳术发展至最高峰,举国上下皆醉心拳术。“虎王”本身更酷爱拳术,曾致力整理日趋繁杂的拳术,并去芜存菁,形成现代泰拳的基本体系。 纵观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明确得出,武学是否昌盛,其根本在于整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点来说,就是官府的态度。 满清政府在渡过三藩之乱后,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回到民间。毕竟人心思明,且不说大批前明兵将隐藏民间,更有天地会等组织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活动。于是,禁武,限武也就成了应有之事。甚至连少林寺都受影响被迫放下棍棒,练起了拳脚。这样的大趋势下,原本在明代传播广泛的器械武学渐渐衰落,拳脚徒手的功夫倒有了更多更广泛的发展空间。 只要练好了拳,器械就玩得好?可实际上是极其错误的认知。如前言里戚继光的话,拳术不过是“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初学入门之艺”。所谓“拳怕少壮,棍怕老练”,实质就是说器械格斗对抗强度高,耗费气力少,更注重于技艺经验。相反徒手格斗由于对抗强度低,耗费气力多,反注重于身体素质。华夏武术即使开发出了例如寸劲这样的打击技巧,但拳头终究不是铁块,它的伤害是冲击性的,而非刀枪剑戟那样具有侵彻力和贯穿力。 例如五代和南北宋时期,很多将领都使用长枪,最重的甚至有记录达到40斤(古代史有记载的第一),但使枪最出名的反倒是杨妙真这个女人。为何?因为枪术上力气是次要的,关键是拿得稳,刺得准!练过剑的都知道,手偏一分,那剑尖就偏开扎点一寸。倘若换成长枪,那偏的就是整整一尺,一尺远的距离还怎么戳中人?要知道骑在马上,本身就不比平地,马蹄踏地,马背上下颠簸,稍一个不稳那就举不平枪杆,枪杆不稳不平,何谈命中呢?倒是在气力上,持枪者借助马力马速,根本无须费力,直接一点一沾就能把目标戳出窟窿,顶个大洞。这方面,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爱好者模仿的骑士刺枪竞技,视屏中仅仅是对冲时慢慢的一点一沾,就直接让枪杆撞盾牌撞到弯曲断开。 所以说,器械这玩意,不同于拳脚,它只有两个字“稳”和“准”,练习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无非是日练夜练加苦练。所以戚继光才说“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也就是说你要肯花时间苦练20年枪法,那肯定能成大器。再譬如俞大猷,他年老时就上书朝廷要求继续留任,还声称“试选三十好汉,各提枪棍,以猷一人独当,不令其披靡辟易,请就斧钺”——《正气堂集·卷二》 因此拳脚功夫其实是小道,练好了也不过是十人敌,器械那才是国术的正道大道,练好了就是百人敌!可惜,满清禁了民间持有兵械,华夏武学也由此渐渐沉沦,国术师傅们转而着迷于当初戚继光看不起的拳脚小道,或开发出千奇百怪的奇门兵器来,就连少林也从公开演武转为地下练武。当然,他们也的确钻研出了成绩,那就是如万花筒一般的武学门派流派,但这些个玩意儿显然愈发脱离战争,更加接近体育运动了。 离开明朝,走近满清,让我们来探究下国术的众多流派。总的来说,武术流派的产生有以下原因: 实战的技术动作都是遵循战争的规律设计的,简明实用,整齐划一,很难形成什么流派。而当武艺随着热兵器普及逐渐同实战有了一定的差距,也便摆脱了这种束缚,从而形成流派。 各地人们的身体条件和自然环境有差异,导致架势套路的变化 不同武术理论的出现,引出了新的武术流派。 第一个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譬如太极拳,就是在明朝末年战将陈王廷解甲归田,回到其家乡河南温县陈家沟后编创的,该套拳法显然吸纳了军中教习的格斗技法,譬如戚继光的拳经三十二势中,太极拳采用的就多达二十九势,许多动作从形式到名称都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 第二个也很好理解,南拳北腿就是这么衍生的,盖因南方人不够高大,腿脚不长,所以武学上讲究贴身近打,武理上更讲究刚劲主动。而北方人因为长大,所以更要发挥自己腿长的优势,进而衍生出“手是两扇门,全凭腿踢人”的路数来。 第三个,最典型的就是内家拳和外家拳,再譬如不走寻常路,专攻下三路的狗拳,地趟拳,这些显然不可能是发源于阵战的武艺,是典型的擂台打斗技,跟格雷西柔术倒有些共同语言。 地域的封闭性,禁武禁教的律令化,以及反清复明的思潮,让清代的武学既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又呈现闭门自守,近亲繁衍的退化姿态。举个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梅花桩。最初的梅花桩是作为习武初步的使身桩,步法规范法,标准化得动力定型,以及提高身体控制能力和平衡能力的方法。举例来说,一般而言,两脚跨立距离越开一些,人就立得越稳。于是人就形成了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搏击时往往两腿越站越开,但这越站越开却是武术一大忌,它影响人步伐移动,重心转移,退却进攻的速度。 曾有一民国武术家指导学生练功,让其两脚踝处栓一条绳子,绳子的长度,就是步伐允许的最大距离。练不了多久,站大步的毛病就可以改掉,这就是一种动力定型方法。再譬如拳击,就有教练用胶布在学生脚后跟上贴石子,这样想放下脚跟也放不下,跳上几天,就习惯了前脚掌着地的步法。可惜在民间武学半文盲那口口相传的背景下,很快梅花桩的用处就被搞歪了,后来越拔越高的梅花桩,完全是为了贴合“无限完美”的艺术要求,成了花哨的表演。 说到表演,那就不能不提到武术套路。事实上,武术套路大量出现基本是形成于满清,当时各种拳社组织主动或被动地同宗教组织相结合,导致巫术风气蔓延。《高宗实录》卷203云:国噜子“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清稗类钞·义使类》云:白莲教教首王聪儿“善幻术,工技击”俞蛟《临清寇略》云:清水教首领“教习拳棒”,却又称“遇异人授符箓,能召鬼神诸邪法”《拳事杂记》载:义和团习武“作拳势之后,便往来舞蹈,或持竹竿……短者以当双剑,单刀,各分门路,支撑冲突,势极勇悍,几于勇不可当”。“欲演拳势,即时手舞足蹈,颇极超距之能,退时则一辑而罢。”由此可见,义和团画符念咒之后,演练的就是套路。这也证明了武术的套路,其实坛脱于亦巫亦武亦舞的“戏”。更有甚者还参杂了各种会道门把戏,譬如劈空掌,碎心掌等等,其实都是骗人的。王选杰《大成拳宗师王芗斋轶事》中就说到某个卖艺的当众表演隔空五步把徒弟打晕了,然后王芗斋劝他不要搞这些鬼把戏,谁知那武师大怒,问王芗斋敢不敢领教他的百步神拳。王芗斋笑着让他直接对身子打,谁知这一拳却使那拳师自己弹了个仰面朝天。 大概自那个年代起,国术就越来越脱离了杀人术,相反在嘴炮术的等级上倒是突飞猛进,甚至到杨露禅那个年代更是各种不着调的说辞,什么“发石如炮”“踏雪无痕”啊都来了。 这套吹捧的体系还绵延至民国,据《形意名家宋铁麟》一文中介绍:山西武术界多将形意大师宋铁麟说成是具有神奇功夫的武术名家,会提气腾空,墙上挂画,即身子向上一纵,能以背、手、足吸附在平滑的墙上。对此,宋本人的回答是“我与其它武人一样,不会腾空,也不能墙上挂画……对于这些奇谈,我们不必荒废唇舌。”从武术到舞术,从开放到封闭,从器械到拳脚,这便是国术在满清黑暗时代趟出的大圈。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尽管清代统治者禁止练武,实战武学器械武学等不断没落,民间则以“社”“馆”的秘密结社形式传授武艺。但称其为国术的成熟期,却无不妥,概因著名拳种如太极,八卦,形意,八极,劈挂等都是清代形成的。 太极拳之所以能广为流传,不是因为它最能打,而是因为它的思想内涵最高明,发展方针最正确。早在百余年前,太极拳家在《十三势行功歌》中就说“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由此可见,当时有眼光的武术家已经意识到,随着热兵器的不断成熟发展,传统冷兵器及其相关技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是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显然,太极拳研习者们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改,大改,要与时俱进的改!于是,以太极拳为代表的一系列武学,随着时代变迁主动演变成为一项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譬如杨露禅为了适应一般练拳人的需要,逐渐删改原有发劲,纵跳,震足和难度较高的动作,并由其子修订为中架子,又经其孙杨澄甫一再修订,遂定型为杨式大架子。 由于练法平正简易,故成为现代最为流行的杨式太极拳,也就是公园里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常打的健身太极拳,更是网文洪荒年代里那些小说主角们必学的奇功绝艺。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又能养身又能打的功夫?那练成了也是一个半吊子,要么选择能打,要么选择养生,这世上可没两全其美的法子! 国术的问题是沙石俱下,里面正确的有,错误的也极多。譬如各种拳家的练功药方,里面坑爹的东西数不胜数,举例某铁砂掌练功方,居然是用铁砂泡醋,还要用泡出来液体洗手后再练功。我说那位空想出方子的大爷啊,这算是啥?吃啥补啥的程序推演版吗?这种问题绝非单独存在,甚至波及面广到《本草纲目》里都有记载。大家可以查查《中国医学大辞典》,里面也记载了一条方子,叫做古线治伤方。其实质呢就是用古代铜钱入药治病,被视为治跌扑伤损的,要求是半两古铜钱5个,火锻醋淬49次,甜瓜子5钱,真珠2钱,研磨,每服一字剂,好酒调,随上下,食前后。哎呦我的大爷,还醋淬七七四十九次呢!我看这么搞下去,拳术家干脆关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个七七四十九天得了,指不定能练出火眼金睛呢!考虑到古代普遍的迷信思想,以及拳术家的文盲半文盲本质,这类半巫半医的方子盛行也完全可以理解,那些练功练出一身伤病的古人,我只能说——走好,没有科学就是这么痛苦! 如前言中所说,军旅武术是“开大阵,对大敌”的格杀技术,强调“队列在前”,“一齐拥进”的配合格斗。其目的是杀死敌人。技术内容以长枪,大刀,弓弩等兵械技术为主体,拳法背视为“无预於大战之技”。但传到清代,戚继光鸳鸯阵里面的器械合击技法已然失传了,现在流传的那些个器械武技也毫无配合格斗的内容。 至于民间武术,那都是“场中较艺,擒捕小贼”的对搏术,讲究“人自为战”,充分发挥个人的技能和体能。技术内容以拳术为主体,兵械多取单刀,剑,棍,花枪等较军阵格杀兵械短,小,轻便者。整个明清时间段,民间武学广泛地吸取古代医学,导引养生术,古典艺术等,朝着内容庞杂,功用繁多的方向发展,当具有较多体育因素和娱乐因素的套路运动成为武术主要的运动之一时,民间武术发展成了一项体育运动项目。对,你们没看错,到清末明初,国术实质上已经被发展成了一项体育健身运动。至于民国时期的武学大昌盛,大繁荣,用一句不客气的话说,那是最后的疯狂! 为何呢?“国难思贤臣,卢瑟爱超人!” 清末民初武学运动的兴起,其实质是中国外战的悲剧性折射,近代史那一斑斑的屡战屡败血泪为国术运动打开了空间,淌出了浸血的河流。因为那时候的国人,已经绝望到必须把期望寄托在老祖宗传下的武艺上了!我很难想象,那批玩着“神打”,搞着咒术,自信辟邪辟炮子的义和拳武术家们,在面对洋枪洋炮时是作何感念?是绝望,是愤怒,还是无奈? 当淮军练勇在面对日本铳枪术的刺刀冲锋时,当李鸿章听闻自己的起家班底被日军凭组织近战冲溃时,是绝望,是愤怒,还是无奈?我想,大概是无奈居多吧!当祖传的武艺再无法为拳术家们“安身立命,博取功名利禄”的时候,武学也就从一门技击术,彻底转为了体育运动,转为了一门空谈的嘴炮术。或许还有企图证明中国功夫的技击家,但这对历史大势毫无作用,于是“强身健体,强国强种”,也就成了国术最后的遮羞布。 幸运的是,武学的悲剧,正是武学交流繁荣的喜剧。当“绝艺奇功”不再是吃饭的家伙时,自然也无须保守,无须秘传,民国武术界的交流繁荣,从某种角度看,正是武学末路的绝望所致。只可惜,这种绝望到和平的年代,反被某些人解读为“武学的大高潮”“武术界的大繁荣”,对此我只能表示十分遗憾。 但很快,抗日战争就连武学这一片最后的遮羞布也扯了下来。事实上在1940年后,再无一本武学刊物出版,因为抗日中的实战结果表明,大刀队终究不敌科学训练的刺刀阵,也就玩玩奇袭而已。而日本的这批精锐刺刀兵,则在太平洋战场被手枪和汤普生冲锋枪科学的虐杀成一团烂肉。说起来,这也算挺搞笑的,中国古代武学一向以枪为尊,日本则一贯以刀为尊,结果在抗日战场上,玩枪艺的反而是日本,玩刀艺的反而是中国。这种现实的嘲讽,真不知道那些躺在地下的武学家们作何感想? 现在扯武术是杀人技的,纯属脑子不好使。是他杀过人还是他的师父杀过人?既然都没有杀过人,这TM不是扯淡吗?毛伯伯说过:实践出真理!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有些人没有。 每个习武的人都有一个大侠梦。有的人知道这是梦,而有些人活在梦中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js/4781.html
- 上一篇文章: 可盐可甜,这个地方必须拥有姓名拍拍照
- 下一篇文章: 中华汤药方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