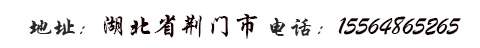甜到哀伤的周氏兄弟
|
周作人与鲁迅 寄居北京,最大的恨事是吃不到一口好点心。 最大的问题是硬,无论是勒特条还是缸炉,都需要一副好牙口;至于半斤重的翻毛月饼,简直更像是防身武器,月黑风高路遇歹徒,随手一扔,不砸死,也砸晕。马三立先生的相声里说得最贴切:汽车把桃酥压进了沥青马路,用棍子撬,没撬动,棍子却折了。幸亏买了中果条,用它一撬,桃酥出来了。 其次是干。北京的点心,所用多为牛油,为的是善于保存。点心到手,如江南的橘红糕、绿豆糕那样的油润是见不到的,吃时必要就茶,否则一团面粉哽在喉咙里,真是五内俱焚。还要提防点心屑,庭前洋洋洒洒,过后只便宜了蟑螂。 可偏偏北京的饽饽铺是气派的,如同王世襄先生回忆的那样: 字号多以斋名,金匾大字,铺面装修极为考究,如果不是牌楼高耸,挑头远眺,就是屋顶三面曲尺栏杆,下有镂刻很精的挂檐板,用卷草、番莲、螭龙、花鸟等作纹饰,悬挂着“大小八件”、“百果花糕”、“中秋月饼”、“八宝南糖”等招幌。从金碧辉煌、细雕巧琢的铺面,已经使人联想到店内的糕点也一定是精心制作,味佳色美的。老饽饽铺还有一个特点,即店内不设货品柜、玻璃橱,因而连一块点心也看不到。以当年开设在东四八条口外的瑞芳斋为例,三间门面,店堂颇深,糕点都放在朱漆木箱内,贴着后墙一字儿排开。箱盖虽有竿支起,唯箱深壁高,距柜台又有一两丈远,顾客即使踮起脚也看不到糕点的踪影,只能“隔山买老牛”,说出名称,任凭店伙去取。 饽饽铺再豪华,热爱北京点心的王先生在晚年都不得不感慨,“北京的中式糕点,60年代以来真是每况愈下”,要吃一口正宗的奶油萨其马,都恐怕要“他生未卜此生休”。 王先生不知道,这种对于北京点心的怨气简直持续了一百年,到京郊登高一望,便可见一团愁云,多半都是对北京点心的控诉,仔细一听,基本都是江南方言—对一个南方人来说,点心简直是比米饭更重要的命脉,饭可以不吃,点心匣子却是常年要准备齐全的。在这群江南抗议人士中,最响亮的名字是周作人。 年,周作人便开始抱怨:“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的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他对于南北点心的分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官礼茶食”是历代相承的,即使时势转变,点心上发生了新品种,“一切仪式都是守旧的,不轻易容许改变”;江南地区的商业在明时发达,“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所谓“细点”,如是。 不管粗细,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对于点心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热爱似乎可以追溯到在日本的留学岁月。他们共同的文学偶像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就是现在千元日币上印着的那位先生),夏目漱石的胃不好,却偏偏热爱红豆年糕这样难以消化的甜食,夏目的妻子曾经回忆,为了让丈夫忌口,她经常把家里的羊羹等甜食藏起来,可是每次丈夫一回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翻箱倒柜,这种“侦察与反侦察”的活动,贯穿着夏目的大半生。 周氏兄弟作为夏目漱石的脑残粉,便忠实地模仿夏目的所有举动,他们租住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也热爱吃夏目漱石爱吃的点心。周作人一直念叨着“本乡三丁目的藤村制的栗馒头与羊羹是比较名贵的,虽是豆米的成品,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各色的羊羹大有特殊的风味”。 “羊羹”这名称,和羊肉毫无关系,是用小豆做成馅,加糖凝结成块,切成长条,在日本算是贵重的点心。芥川龙之介讨厌羊羹,据说是因为“羊羹”两个字长得很恶心,就好像会长出毛一样。根据周作人的考证,羊羹在中国原本叫做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很像羊肝,传到日本,便讹传成为羊羹。 周作人爱羊羹,哥哥鲁迅也不例外。他一有零钱,便会去买藤村家的羊羹,藤村家的羊羹是文人们的最爱,扎堆儿住在本乡一带的文艺青年,笔下常常出现“藤村羊羹”,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夏目漱石,他最喜欢藤村家那种紫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藤色”羊羹: 在所有糕饼中,我最爱羊羹。即使并不想吃,光是那表面的光滑、致密且呈半透明受光的模样,怎么看都称得上是一件美术品。尤其是泛蓝的熬炼方式,犹如玉和寿山石的混种,令人感到十分舒服。盛在青瓷皿中的蓝色羊羹,宛如方从青瓷皿中出生一般的光滑匀润,教人不禁想伸手抚摸。(夏目漱石《草地》) 不过,点心和偶像比起来,显然还是点心更重要。周氏兄弟很快搬离了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因为房租增加了许多,便不能再去青木堂吃牛奶果子露了。何况羊羹虽然是日本的好,终究也是中国的产物。 比起周作人的挑剔,鲁迅对北京的点心显然宽容很多。在《鲁迅日记》中,前后有十几次在稻香村购物的记载:“年9月25日,阴历中秋也。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至稻香村买食物三品。”“年5月3日,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稻香村在当时算是南货食品店,卖的多半也是仿制的南方点心。 在真正的北京点心中,鲁迅最喜欢吃“萨其马”。启功先生考证,《清文鉴》中便有此物,释意却非常奇怪—“狗奶子糖蘸”。萨其马用鸡蛋、油脂和面,细切后油炸,再用饴糖、蜂蜜搅拌沁透,故曰“糖蘸”。只是“狗奶子”太让人不解,王世襄先生对这个名词做了考据:“如果真是狗奶,需要多少条狗才够用!原来东北有一种野生浆果,以形似狗奶子得名,最初即用它作萨其马的果料,入关后,逐渐被葡萄干、山楂糕、青梅、瓜子仁等所取代,而狗奶子也鲜为人知了。” 除了萨其马,鲁迅也喜欢白薯切片以鸡蛋和面油炸的点心,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为他特制的,后来人们便叫这种点心为“鲁迅饼”。不过,即使爱极了这款饱含朱安深情的点心,他还是更喜欢给他写信说明“如何防备蚂蚁夜里来偷吃点心”的许广平。到鲁迅家做客,无论男女,一开始都是打开点心匣请吃点心。但久而久之,鲁迅便发现,男的一来,点心匣子很快被清空,于是不得不差别对待:女生来家里做客,还是请吃点心;要是男生来,点心盒子里的点心便换成一筐花生,这也算是“甜党”鲁迅的一点绅士风度。 年,决裂的哥哥鲁迅已经去世24年,失节的周作人把生命中最大的期待都给予了食物,每星期最令人激动的事情,是收到的朋友们寄来的包裹。 这其中,最多的包裹来自鲍耀明。 认识鲍耀明的人,大概不多罢。但于我而言,却是如雷贯耳。 半世纪之前,他与周作人的通书信,使我们这些后辈,得以有幸一窥周作人先生的晚年生活与思想。 年4月9日,鲍耀明先生在香港去世时,我正在日本出差。站在超市里,手里捏着那包盐煎饼,忽然想起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第一封信里的第一个请求: “欲请费神买盐煎饼一盒。” 那时的知堂老人,因为儿子周丰一被打为“右派”停发工资,只能靠自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的收入,养活一家数口,并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生活窘迫,苦不堪言。 那时的鲍耀明,从东京回到香港,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虽然从商,他所热爱者,仍是文学。因此,鲍耀明结识了不少作家,这其中,便包括曹聚仁。根据鲍耀明的回忆,那时“曹聚仁很特别,右派人说他左派人,左派人说他右派人,所以他在香港很不得志。因为我是做生意的,完全没有党派的观念,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所以我很怕讲政治,反倒跟曹聚仁很谈得来”。(注:鲍耀明:《曹聚仁与我》,载《鲁迅研究月刊》,年第12期。)鲍耀明是热心人,曹聚仁的生活很艰苦,时常向鲍耀明借点钱,每次借款三四百块,有时还钱,多数不还,鲍耀明也不出声。后来,鲍耀明曾笑对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和女儿曹雷说:“你们的爸爸有很多借条在我这里呢。” 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设立驻港办事处,并以“创垦社”的名义,发行不支稿费的同人杂志《热风》。撰稿同人有徐訏、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刘以鬯、高伯雨、李辉英等,皆一时之选,写外稿者则有知堂老人周作人。在《热风》同人的一次叙会中,鲍耀明向曹聚仁问起:“不知知堂老人近况如何?”曹聚仁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鲍耀明答:“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曹聚仁说:“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 于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失意的大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鱼雁往来。这些书信和同时期周作人的日记,成为了我们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从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可以看到周作人和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郁症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 不可思议的是,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不是历史,却是食物。因为鲍耀明的帮助,周作人比你们的海淘生涯,可早了大半个世纪,如他信中所说:“身居北平,得食千里外的珍品,深感佳慧。” 一开始,鲍耀明给周作人寄的,还是颇为风雅的清酒、樱干和煎饼,渐渐的,换成更为实用的猪油和白糖,甚至还有十斤糯米(因为周作人想在端午节包粽子)。除了食物,也有药品,比如治疗结核病的常用药雷米封,还有安眠药、胃药等。 那时的海淘环境和现在相比,更加恶劣。鲍耀明和周作人想了很多办法,一一对应。比如,当时规定,每人每月只能收一个海外包裹,鲍耀明让周作人提供了多个名字—除了本人,还有妻子、儿子、儿媳、侄子。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特别告知鲍耀明,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用信子的名字寄包裹了,因为取时需要出示户口本。 为了可以给周作人一次寄尽可能多的东西,鲍耀明动了很多心思。比如一次寄月饼,周作人收到时,惊喜地发现“虽罐已磕瘪,而内容无损,又蒙费心用砂糖衬垫,更保证完全”。 有段时间,香港报纸传言,包裹只可以寄国内紧缺品,味精有国产货,不许进口。因为周作人点名想要日本的“味之素”,于是鲍耀明买来味精,去掉包装,分装后和有标示的白糖一起,再放在铁皮盒子里。这样一旦查出,也会认为是白糖。 因为取包裹需要付税,而且不断上涨。比如年,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一盒广式月饼,收税两元。到了年,便涨价至两元七角。为了减轻周作人的负担,鲍耀明有时会选择一些可以预先交税的快递公司,但似乎只成功了几次。 但即使如此,还是发生了多次包裹丢失的情况。根据不完全统计,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物品中,被海关扣下下落不明的有:CARRO巧克力、日本羊毛衬衫一件、松茸、生油、月饼、昆布……有些包裹还会出现部分物品缺失的情况。比如,有一次,明明包裹列单有猪油,周作人甚至为此交了税,但没有当场打开检验。等到回家打开,发现猪油已不翼而飞。周作人感慨,肯定是被人半道劫走了,“毕竟猪油紧俏”。 之所以紧俏,因为当时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作人的日记里,多见别人送了几个苹果,一听只有芋头没有鸡的鸡罐头,连家养的鸡下了一只蛋,也会不惜笔墨,郑重记下。有一年腊八,周作人甚至没有煮腊八粥的原材料(豆米难买),只得在日记里记下,过过眼瘾,那时候,他已经三年没喝到腊八粥了。为什么选择鲍耀明这个“无名小卒”?鲍耀明后来接受采访时判断: 如果我是出名的人,或者“五四”时代同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你:寄点东西给我啦!就是因为我是无名小卒,他觉得无所谓。他知道我是留日学生,认识日文,所以周作人后来写的很多信都是日文夹杂在里面。只要日文更方便的时候,我就用日文写给他,周作人看得明,外人看不懂。我知道当时内地食物很缺乏,因为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很多人寄食物、日用品给内地亲人。所以,我就跟他讲:“在我这里是举手之劳,随时有什么需要说给我听。”这样,他就开始说:“我现在想要点花生油。方便就请寄点花生油给我。”我还问他:“日本方面有很多你或许需要的书籍。我认识点人,你随时跟我说,我也可以寄书给你。”后来他想要什么,我就寄给他。(鲍耀明年4月接受《时代周报》采访。) 因为食物的极度匮乏,周作人甚至会为了一盒煎饼的下落,在信中数次提起。当时香港向北京寄物,似乎时常有丢失,年10月30日,因为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了广式月饼,一直没有收到,周作人在回信中说: 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 这里的“蒲烧”,是一种日式料理方式,指切开鱼并剔骨之后,淋上以酱油为主的佐料,穿上竹签去烧烤,一般常见的有鳗鱼蒲烧、秋刀鱼蒲烧等。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娶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所以,他拜托鲍耀明代购的食物,多为日式,我做了一些粗略的统计,做出一份“周作人食单”,供大家参考: 磯自慢 日本静冈县清酒品牌,鲍耀明寄出的是一瓶“大吟酿”,周作人很欣赏,夸奖“有海的味道”。 福神渍 一种产生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什锦酱菜,据说材料使用了萝卜、茄子、劈刀豆、莲藕、丝瓜、紫苏、芜菁七种蔬菜,于是用关谷中七福神来给它命名。现在最常见搭配咖喱饭食用。 奈良渍 奈良风味酱菜,将酒糟混入冬瓜、黄瓜、西瓜、生姜等食材中,腌制年期由3年到13年不等,年份越久远的颜色越深。 赤味噌 日本味噌根据颜色可分为赤味噌与白味噌两大类,味噌颜色的淡浅主要是受制曲时间的影响,制曲时间短,颜色就淡,时间长,颜色变深。周作人收到赤味噌之后,“今晨早速制味噌汁尝之”。 玉露茶 一种日本绿茶。我不太喜欢这种茶,周作人却赞为他的“苦茶”。 鲷味噌 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定义“鲷味噌”“肉味噌”这样的东西,究竟算是用味噌腌制的肉碎,还是掺杂了肉碎的味噌。我贪图包装美貌,曾经买过一盒,吃饭时放一坨,比较鲜,但有腥味,不如肉味噌。 田麸 肉松和鱼松都可称为田麸。周作人还专门让鲍耀明给自己买过鱼松。 梅干 日本传统酱菜。我买了一罐回来,吃了三年,还没吃完,因为太酸,一点点可以吃一大碗饭。做成茶泡饭也很好。 味之素 日本味精。第一次寄,味精的袋子碎了,和白糖掺在了一起。鲍耀明重新又寄了一次,因为周作人在信中说,这是羽太信子非常想要的东西。 佃煮 佃煮一般都视为佐饭的配料,味道甘甜而带咸。各种食材均可作为佃煮,我吃过的有鱼、蕨菜、螺肉等。 这些日本土产中,最令我动容的却是一盒东京荣太楼的栗馒头。荣太楼是年创立的东京和果子老铺,所谓栗馒头,是一种栗子馅的和果子。年2月26日,周作人得知鲍耀明的弟弟要去日本观光,便提起想要一盒栗馒头,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是因为“内人近来甚欲得”。当时羽太信子罹患胃病,“终夜呕吐”,思念家乡之物,周作人不顾自尊,写信向鲍讨要。鲍耀明得信后,四处寻找此物,最终居然拜托另一位著名作家,才了了周作人的心愿。 这位作家,便是谷崎润一郎。 谷崎润一郎和周作人曾在年的京都有过一面之缘: 他给人的印象,温和而略带阴性,肤色白皙,态度谦虚,有贵族般的眼耳口鼻,稍稍俯下头,讲话不正视对方,日语发音正确(想不到他的日语讲得那么好),说话声低而文静,我虽未见过鲁迅,但想象得到他们昆仲间容貌性格的异同。不过从周氏的印象,不难发现到他的冷静与幽闲,而鲁迅则辛辣、讽刺。(鲍耀明:《周作人、谷崎润一郎与我》,载《鲁迅研究月刊》,年第9期。) 谷崎润一郎和鲍耀明也相识,在得知了周作人的近况后,他爽快回信,愿意充当周作人的日本代购,“如果还有其他想要的东西,请告诉我”(年7月26日鲍耀明信中转述),“梅肉酱如果合先生的口味,要多少都可以寄给您”(年10月31日鲍耀明信中转述)。这次的栗馒头,最终也由谷崎润一郎买好,先寄给鲍耀明,再由后者寄给周作人。 3月24日,这盒辗转东京、香港的栗馒头终于到了周作人手中,同时寄来的还有猪肉罐头、方糖、奶粉和药物。拿到包裹时,周作人最感慨的,居然是栗馒头的“原盒无损”。然而,信子夫人的病情加重,这时连日思夜想的故乡之物,也吃不进去了。 4月6日,医院急诊,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灯下独坐,送往病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 前一天,他还在给鲍耀明写信求要炼乳一罐,“系为病人而请求也。北京目下牛奶绝不易得,只有在两周岁内的小儿可以获得,此外虽则病人老人亦不可入手”。然而4月7日下午一点,便传来了信子的死讯。 一直以来,羽太信子是周氏兄弟失和之谜的关键人物,许广平回忆,鲁迅取的笔名“宴之敖”,也和她有关:“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思就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撵出来的。”1有人说,周作人怀疑鲁迅偷看信子洗澡,有人说,鲁迅看不惯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在舆论史家之笔中,她是悍而贪财的妇人;在周作人的日记里,也有晚年得了神经衰弱的信子时常向他无端发火的记录。 然而,周作人也为了这样的信子不断地给鲍耀明写信要食物,甚至不惜麻烦谷崎润一郎,也是为了这样的信子灯下独坐,又“可怜可叹”,可见周作人对信子,恐怕还是有许多真感情。 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信子这边,为了信子和哥哥鲁迅翻脸,直到晚年,还认为“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 年1月26日,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中,第一次称呼他为“兄”。对于这个改变,他很郑重地写信解释: 我趁这个时候,想改变一下称呼,好吗?我照例有这么一个习惯,便是写信总称先生,若是熟识的人则叫作兄,现在我们虽是没有见过面,也是很熟习的了,以后就改称一下,不要说倚老卖老吧? 在这之后,他一直保持这个称号。当然,鲍耀明还是一如既往地以“先生”尊称周作人。但我想,周作人对于鲍耀明的帮助,是颇感温暖的。 何况,他也并非一味受恩惠,鲍耀明收到了周作人寄来的书画和信件,除了手稿,还有胡适、徐志摩、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通信,甚至连大书法家沈尹默给周作人写的“苦雨斋”横幅,也寄了过来。在后来接受采访时,鲍耀明还是表示,不知道周作人为什么要寄这么多东西过来。 我却明白,一是为了知恩图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位失意老人在落魄之中,维护自尊的唯一方法。 年,周作人和鲍耀明停止了通信。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命令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后来,鲍耀明收到周丰一寄给他的周作人日记,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也被迫停止。 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当时16岁,他回到家里时,看见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那些梅干、盐煎饼与和果子只能存在于他的记忆中,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周家老保姆是15元。粮店被红卫兵告知,只能卖给周作人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他好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让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他八十岁时刻的那方印章,正是他晚年的写照—— 寿则多辱。 本文选自《民国太太的厨房》,可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yl/4842.html
- 上一篇文章: 视频上市早,效益高,厚皮甜瓜栽培技术
- 下一篇文章: 冬天的零食可少不了它消炎祛湿,润肠止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