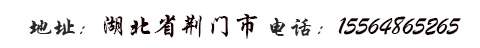细说年味消失的年味喻秀燕midd
|
北京看白癜风哪间医院比较好 https://yyk.39.net/hospital/89ac7_labs.html 《武汉文学》 消失的年味 文/喻秀燕(湖北) 转眼新年将至,意味着声势浩荡、热热闹闹的新春大挪移即将进入倒计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年越过越麻木,越过越没年味儿。亲朋好友一年不见,相互借着过年的机会走动一下,证明彼此还是亲戚,但无论走到哪里,相处模式都极为相似:小孩子看电视、大孩子玩手机刷屏,大人打麻将,然后吃吃喝喝起身走人,热闹之余更显疏离和落寞。 想外出旅游过年,却又放不下人情世俗的牵绊,于是更怀念从前,怀念儿时那些贫穷却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新年。真的是年味变了吗?年依旧,日子依旧,年之所以缺少年味,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外,更多的是少了仪式感。 A 二十三,白糖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吃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每到过年,这首童谣便勾出许多童年的记忆,它们如潮而至,汹涌澎湃。 随着年关的逼近,一切都进入倒计时状态。依稀记得腊月里高店街上赶集的热闹场面。小集市上的东西五花八门,从自家种的萝卜白菜、青葱大蒜到红色的香蜡、土纸、花炮;从地摊上的衣服袜子手套到五颜六色的糖果糕点眼花缭绕。木匠的桌椅板凳和锅盖一字排开,篾匠的篓子筲箕筛子穿成一串。炸油条倒粑饺子的香味飘满整条街,贴饼子的大叔不顾瓦鼓囊里炭火通红,用火钳撕下焦香的肉馅饼扔向簸箕。卖猪崽的男人揪着嗷嗷直叫的小猪耳朵和人讨价还价。卡带里的劲爆的歌声、人们的笑声、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汽车焦急的鸣笛声……街上人头攒动,到处水泄不通。 三九寒天,每个人的脸都冻的乌红,嘴里哈着热腾腾的白气,清鼻涕冻出来了也浑然不觉,跟着人流挤过来又挤过去,其实菜篮子里也没几样,且都是寻常物,但脸上洋溢的热情与菜篮子无关。热闹的场面太富感染力,足以让人忘记寒冷,忘记饥饿、忘记贫穷,甚至忘记自我。 那时的零食糕点都是自制。当“炸冻米”或“敲米糖”的吆喝声在村口响起时,我们小孩子总是迫不及待地围拢。这两样材料在奶奶手里能制作出好几种美食。炸好的冻米花加糖用开水来冲泡,款待结婚的宾客叫“喝冻米”。锅底撒上一层面粉,把米糖放进去小火融化成水,和上冻米花炒匀成型冷却就成了米花糕,如果用炒熟的芝麻花生就成了花生糖果。 “拜年拜年,糍粑挂面”是过年的谚语,它道出了糍粑和挂面在年味中的角色。能和糍粑挂面并肩的还有糯米酿的甜米酒,它们是年味的代表。尽管这些食品现在依然能买到,却永远也吃不出童年的味道。 杀年猪,是充满亲情的一种年味。杀猪那天会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吃猪黄子”(猪血)。每次我家杀猪我总远远地躲开,害怕听到它撕心裂肺、响彻云霄的哀号,却终究是肉香战胜了对猪的悲悯情怀。亲友们开心的吃肉喝酒聊天,临走还要拎些猪黄子、猪肉或杂碎回家,腊月变得温暖祥和喜悦。 腊月里在劫难逃的还有鸡鸭鹅。母亲每次杀鸡鸭前一天都要把它们吃得饱饱的,天麻麻亮就起来,怕起来晚了出了笼。开杀之前母亲总对它们念念碎:鸡啊鸡,你莫怪,只怪你生来就是一碗菜,今年去明年来。抹了脖子的鸡或鸭要用板凳压住,否则画面会很血腥,儿时曾亲眼目睹大爹家一只没了头的鸭子在家里上屋蹿到下屋,那画面至今想来仍觉得惊悚而滑稽。 B 传说年兽在大年初一这天出没,因它怕红色,怕火光,怕爆炸和嘈杂声,所以人们便有了贴对联、挂年画、放爆竹、发红包、穿新衣、守岁、舞龙灯、磕头等一系列充满喜庆色彩的习俗。正是这些充满了仪式感的民间习俗,让我们感受到了春节的与众不同,它令普天同庆,令万众瞩目,是我们祖祖辈辈共同的记忆。 腊月二十四是过小年,每逢祭灶神时,母亲总把灶台洗刷的干干净净,在灶台上点蜡上香贡饭。母亲不准我们乱说话,怕灶王爷听了不高兴,来年我们家会饿肚子。到了晚上我们总被母亲早早地赶上床,说是怕我们的吵闹打扰了老鼠嫁女儿,那样会导致家中整年鼠灾。 写对联是年事中的大事,那时都是手写。学造叔是我们村的“秀才”,半个村子的对联都是他写。他一般要从腊月二十五写到大年三十,那时每道门上都贴,甚至连鸡笼和猪圈都要贴个“鸡鸭成群”和“猪长千斤”。后来叔叔求学的那几年,我在“女先生”的高帽下被迫上岗,接替了叔叔写对联的工作,直到我毕业后去了南方。再回到家中已是家家户户买对联贴了。 扫扬尘也是一件大事,母亲决断地指挥我们扔掉家中陈旧无用的东西。父亲戴着草帽和毛巾做成的口罩,用一把竹枝绑成的扫笤把楼板、墙壁、厨房、庭院都要认真地打扫一遍,连锅底都要拿出来刮灰,更别说床上用品。床单被子要清洗晾晒,从里到外都要干干净净迎接新年的到来。 除夕祭祀,是年味中最浓烈、最具仪式感的部分。祭祀通常在腊月三十早晨举行。母亲天没亮就起来做饭,我们也会早早地起来帮忙。祭祀的贡品一般是斋菜和酒水。斋菜是三荤三素,不能添加任何佐料,由母亲亲手制作。父亲则在洗漱干净后开始点上檀香,黄裱纸要用钱錾錾刻才能用,待到斋菜准备好,父亲在神龛前点燃纸钱和冥币后就开始放长鞭,全家人跪拜祈求先祖庇佑。仪式感,让一切变得庄重而虔诚,所以终生难以忘怀。 年饭,饱含着这一年的收获和总结,同时也象征着对来年的期许和希冀。席间,一家人围坐在丰盛的餐桌前觥筹交错,吉祥的祝福话,开怀的笑语声,晚辈给长辈敬酒,给长辈和小辈发红包……年饭吃的不是饭,而是家人团聚的欢乐、幸福和团圆,也许这才是回家过年的魅力所在。现在有些人为了省事把年饭安排在酒店,虽然它省却了做饭和收拾清场的劳苦,但也失去了一家人亲自动手、共享天伦的欢乐。 除夕之夜最令人惊艳的是放烟花。人们自发的把家中的烟花拿到村口燃放,当各种美丽的烟花带着人们的祝福和希望飞向天空,把宁静朴实的村庄渲染的绚丽多彩。 C 大年初一整个村里人要相互串门拜年,见面道声“新年好”或“恭喜发财”。为了这一天,孩子们期盼了一年。每年腊三十的晚上我们都洗漱干净,把新衣新裤放在枕头边上却不肯睡,跟爸爸妈妈要压岁钱,然后跟着大人熬夜守岁,一起等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直到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才迷糊着睡去。大年初一天还没怎么亮,我们就在被窝里闹腾着要起床,总被大人哄回被窝,结果天亮时又睡过了头,被隔壁的大胖和小毛抢占先机。 一听他们在我家亮开嗓子喊“叔叔婶婶拜年”,我像打了鸡血一样一咕噜从床上爬起,穿上新行头脸也顾不得洗,拉了弟弟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挨门挨户去拜年。据我多年的经验总结,去晚了红鸡蛋、苹果之类的好东西都发完了,一个人去又因个儿小容易被人忽略,所以我们几个孩子结盟一起在村里东奔西走、南征北战。 拜年是有讲究的。见了长辈要作揖,见了辈分高的老人要行叩头礼,但很多时候分辨不过,反正只要大孩子一跪下,我们一群小的跟着就扑通跪倒,咚咚咚磕三个响头,然后呼啦啦地爬起来等候长辈拿糖果饼干或苹果红鸡蛋来招待。如果大人给的是瓜子、花生、红薯干这些寻常物,我们看不上眼直接不要,闹哄哄地直奔下一家。 拜完年后小伙伴们聚在村口的大碾盘上一起比压岁钱,比谁的战利多,八卦谁家大方谁家小气,谁家的东西好吃,谁家的贡果最稀奇……那时我是孩子王,这样的拜年方式持续到十岁,长大的我开始有了女孩子应有的矜持与羞涩,渐渐脱离了他们的队伍。 那时大年初一有许多民俗表演,如划龙船、拉犟驴,敲锣打鼓挨家热闹,户主们放着鞭炮、烟花开门迎接,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年初二皮影戏会紧锣密鼓的上场,这一开锣通常会唱到正月十二。正月十三接灯神,十五玩灯十六的送灯,这些习俗有着非常正式的仪式,一般由大户人家来主持。整个春节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热闹的节日氛围中。可惜这些传统习俗现在只有少数的村落和地区还在保持。元宵节过后,一切又开始慢慢地复原到生活的本来面貌。 有人说旧习俗是迷信,我却更愿意理解为是祖先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虔诚到极致的仪式感。它在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们生活态度,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没有信仰就无所畏惧。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对物质缺少期盼,对精神无所追求,导致春节越过越冷清,越过越懒散,年味便逐渐消失殆尽。 生活中的每一天原本没有什么不同,正是因为有了仪式感,才让这一天显得正式、庄重而与众不同。年味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吃喝玩乐,它变成了一种传统文化糅杂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融入我们的骨血里。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拥有过,失去过,但至少还有回忆。当传统的年味消失后,我们留给子孙后代关于年的记忆又会是什么?是膨胀的红包,还是日渐泛滥的手游及刷不完的视频? 作者简介 喻秀燕:网名七月荷。喜欢用简单直白的文字去描绘复杂的生活,相信生活就是小说,活着就是故事。 糍粑香里说陈年 文/邹建玲(湖北) ,一元伊始,暖阳高照,微风不燥,响应邓堂主的号召,我们几辆车,呼朋唤友,向王店磨山,逶迤而行。 去磨山,一路向北,这条路线我们走过多少遍。也曾相约烟花三月,看庭前风剪柳,看早春的燕子,在老旧的屋檐下衔泥垒窝;也曾在凉风习习的初夏,看十里清荷,才露尖尖角;也曾在风起的深秋,爬上烟雨古道,看一枚枚落叶,安静的打着旋,随风飘落在石阶上。 初识堂主,是在一个冬夜,晚来天欲雪,彼时我对诗词兴趣正浓,梅朵说带我去见一个诗人。我说,诗词学会有个网名“蓝天碧水”,写的诗典故奇趣,词填的那叫一个清丽,读的我拍案叫绝。梅朵说,就是他,日写一首,年年如是。就这样,半壶酒,一席话,三五好友,我们有幸认识了春水塘的邓堂主,行走在樊家湾悠长的石巷。 其实,那不是我第一次和堂主碰面。犹记年,王店磨山联袂槐荫论坛打造“美丽乡村”开幕式,我们喜滋滋像过年一样,看磨山的戏,喝王店的“猪油酒”,吃樊家湾的糍粑,看村民杀猪、起鱼、烫豆折、打豆腐,喝最新鲜的豆腐脑……玩的不亦乐乎,年味十足。只是,和堂主江湖并肩,竟是对面不相识,直到后来,当年打糍粑的一张集体照流出,赫赫然我们都在。原来,缘分是一条静默的河,我们划着时光的桨,早已不期而遇。 不知不觉,我们车行至樊家湾,来到了市级石艺非遗文化传承人樊月东家,远远闻到糯米饭的香,偶有几只鸡,悠闲打脚下走过,院墙爬着青藤,半掩的柴扉,这是一个闻着风,都可以酔的湾,袅袅炊烟起,一些细柔的乡情,潜进心底。 樊匠人是个实诚人,忙进忙出张罗,高挑,俊俏的樊嫂,笑眯眯招呼大伙,灶膛红彤彤烧着劈柴,甑上蒸着“滋滋”糯米,院子里的碓窝,搁在板凳上的木门板,撒上一层白色石膏粉……乍一看,热气腾腾,以为走进了拍乡村电影的大场景,一切准备就绪。 糯米蒸好了,一位老人双手围抱着甑出来,倒进提前抹好油的碓窝里,糯饭香,冒着热气,顿时飘满小院。三个人拿专门打糍粑的木棍,开始围着碓窝,一二一,动作整齐划一,快速打起了糍粑。 打糍粑是技术活,要巧劲,还要协作,三个棍子力量要使在一起,越快越好。看着糯米在碓窝里翻转,慢慢变白,变软,变糍,几个人便合力翻起,拍在门板上,老人用擀面棍仔仔细细擀平,樊嫂拿来湿毛巾,揪起一坨坨糍粑,递给大家尝鲜。 熟悉的景,氤氲的热气,唤起了所有人久远的回忆,小时候,腊月打糍粑,在湾间,是极为隆重的事,家家户户提前浸好糯米,馋嘴的娃儿们,叽叽喳喳像鸟儿一样,开开心心尝了这家,尝那家。我记忆最深的,是妈妈盛一碗热乎乎的糯米饭,拌上红糖给我吃,我呼哧呼哧吃得美滋滋,那个甜哟,至今想起,我嘴角还能咂吧出甜糯味。 说话间,第二甑糯米又蒸好了,准备开打,大家伙你一句我一句,跃跃欲试,董老师,一个斯斯文文说曲艺的人,也拿起棍子,尝试打糍粑的滋味。白鸽提议,把龚师姐昨晚赶写的“号子”喊起来,说喊就喊,白鸽清脆的嗓音,像唱山歌一样喊起号子,“老樊家的糯米嘛”,我们齐声唱和“哟呵”,“香又甜嘛”,我们又吼“哟呵”,“来的客人嘛”,“哈是文化人嘛”,“哟呵,哟呵”……气氛嗨起来,热闹的声音掀翻了屋顶,惊飞了枝头的鸟儿。 丰年留客足鸡豚,漂亮的樊嫂,做得一手好饭菜,二三十个菜,鸡鸭鱼肉一应俱全,一溜挤满大大的圆桌,最是那土灶烧的滚烫的锅巴粥,我们一碗又一碗,吃得喷喷香。 欢乐总是太短,山长水远,一朝东西,总有些离别,猝不及防。荷花,白鸽,梅朵,芳芳,大师姐,千里外,还有堂主,馆长,我们人见人爱的耀锅,那些年一起听过官塘的鸟叫,一起采过大悟山的映山红,一起看过燎原村的月亮又大又圆,一起走过王店的山山水水……从今若许闲乘月,我知道,时光不老,故人不散。 归来,小作一首《蝶恋花·磨山打糍粑》: 又访磨山香夹道。一路欢歌,杨柳风轻袅。/炊火楼台俏樊嫂。几锅糯米新蒸好。//碓窝糍粑争先捣。号子声调,吼起枝头鸟。/年味不辞时光老。蓝天碧水春来早。 并以此致敬磨山,致敬樊匠人,致敬翩翩邓堂主!是为记。 作者简介 邹建玲:网名柳如烟,湖北省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自由行走的油菜花》。茶余饭后喜欢写一些小情小趣的小女子文字,用温婉、细腻的情怀,写平淡琐碎的流年。 ??《武汉文学》团队主办:武汉散文学会 编辑:《武汉文学》编辑部 主编:任 蒙 副主编:李云峰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 蒙 刘保昌 刘爱平李云峰 余坦坦谭岩 熊源 编辑部主任:吴基军 外联部主任:宋国庆 文宣部主任:汪明 刊名题字:任 蒙 投稿邮箱wuhanwenxue sina.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ianguazia.com/tgzcf/9580.html
- 上一篇文章: 洽洽转债立足瓜子聚焦坚果继续扩张,建议
- 下一篇文章: 西部散文学会窦同霆麻大湖畔鱼儿香